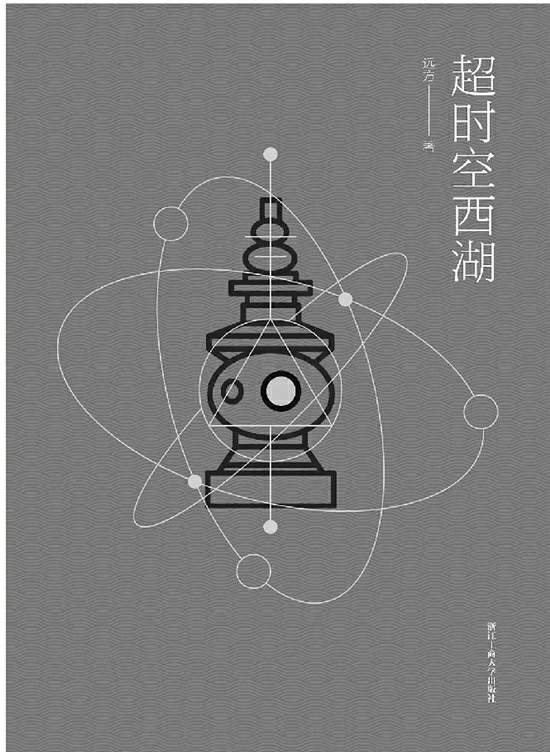2012年2月,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出版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该项目的唯一一位国家级传承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猴场镇打哈村打望组人陈兴华,作为传承人代表参会。次年,陈兴华开始着手翻译整理自己的史诗唱诵版本,四年时间记录整理三万八千行史诗,以此作为自己传承工作的依据和工具,这也许是非遗国家级传承人当中的唯一。凭借对精神信仰的长年坚守,对史诗传承的勇敢担当,陈兴华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了翻译文本书稿,向这位锐意探索和坚持不懈的传承人致敬!
传承非遗民间觅新径
贵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主持人语
一部传承人的史诗大作
余未人
一部《亚鲁王》史诗汉文意译打印稿放在我的案头,长达三万八千余行。它是由七十二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陈兴华个人整理的。
完成这部史诗,他修改了六稿,花了四年时间。陈兴华只上过小学一年级,他从十几岁起,就把这部篇幅浩瀚的苗族史诗一段段铭记在心,并在麻山的苗族葬礼上唱诵了几十年。单单这个本领,就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谜团。
进得麻山,一座座突兀的山峦扑面而来,这里有着喀斯特地貌独有的肃杀与荒凉。每当乡间有“事”的时候,山寨就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唢呐和爆竹热络喧闹,陈兴华等东郎(苗语音译,歌师之意)彻夜唱诵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带来了远古的文明气息。此时,山寨将其不同寻常的大美一一呈现于世人。
东郎是一批孤独、悲壮而顽强的苗人。在古老的葬礼上,长髯飘飘的东郎陈兴华一反平日的拘谨和谦恭,引吭高歌,器宇轩昂地主导仪式。在一场场葬礼上唱诵着凝重、激越、悲怆的英雄史诗。几十年光阴累积的奕奕神采,都在这一刻飞扬起来。如果没有《亚鲁王》史诗的传承,他的人生不会有如此的华彩。
只要接触到麻山的东郎,就会让你震惊、感动,有时热泪盈眶。然而,在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感动是无能为力的,文化工作者只有用自己的思考、行动和文字,才能成为孤军奋战的东郎们的坚强支撑。
面对这部五言体的亚鲁王史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晓东、亚鲁王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江、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唐娜和我,确实感慨万千——这是一部由传承人陈兴华独立翻译完成的大作。陈兴华在史诗的形式上、传承方式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特别令人钦佩。在对陈兴华五言本进行了多方面介入、研读后,我们分别撰文。以下,就将成果与读者分享。
(余未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省文史馆馆员)

杨正江与陈兴华一起唱诵“亚鲁王”
2009年的秋天,紫云自治县工会主席伍兴荣到我们亚鲁王工作室慰问临聘的农民知识分子杨松、吴斌二人,给我们讲述他母舅陈兴华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带着中央民院的教授进入麻山,用录音磁带记录史诗《亚鲁王》的感人事迹。
他告诉我们进入秋天的某一天,母舅陈兴华在县电视台上看到《亚鲁王》申遗的新闻报道,听到了久违的史诗唱诵声音,来自麻山的东郎真实地进入了电视,他放下了手里的碗筷,潸然泪下。他颤抖着手指拨打侄子伍兴荣的电话,要求其引路去见见亚鲁王工作室这群青年人。
那一天,午后的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到了翻译工作室,静谧地照在摆放电脑的小桌上。陈兴华来了,他穿着一套灰色的休闲西装,白皙的脸庞泛起一丝红润,轻声礼貌地问“杨正江老师在吗?”我起身迎上去紧握着这位老人的手,他瞬间热泪盈眶。我们亲切地叫他一声“陈伯伯”。
是什么力量让这位老人执着地要过来工作室看望我们?是什么情愫让他见到我们时就已经泪流满面?
陈兴华在麻山经历岁月,见证着麻山。他心安地在县粮食局度过中老年的公职生涯,退休之后,计划着安度晚年。在电视上看到那一条苗族史诗《亚鲁王》申遗的新闻,唤醒沉睡多年的内心。当他看到我们这一群青年人的执着,仿佛回到了他年少时代的风采。
七年来,陈兴华始终坚持如初地陪同着我们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很多的古苗语,陈兴华只会说却不懂得其义,若干的苗语,他不知道如何用汉语来表达。他认真努力地阅读着我们翻译的初稿,学习拼读苗文,学习用电脑,学习翻译。他带着录音笔重返麻山的葬礼现场,在实践中点点滴滴地记录与回忆,慢慢地积累,陈兴华自己尝试翻译的世界渐渐地丰富起来。
再后来,我们开展了抢救与传承保护工作,这一群青年队伍不断壮大,工作的规模不断开拓。连续走访一千七百多名东郎,建立了二十四个传习基地,而陈伯也仅仅是其中一个传习基地的负责人。
唯有自己开拓更多的生存智慧,方能求得文化的尊严。我们持一颗文化良知之心,做文化人的本职工作。是无数名像陈兴华一样的东郎赋予我们的奇异力量,突破了千难万阻,成就了一份事业。
寻找久违乡音
建传习基地
杨正江

余未人在麻山地区采风调研
陈兴华的学艺道路,就是在险途上的探索。《亚鲁王》唱诵历来有一徒拜一师的古规。所以,大多数歌师只是能够依照古规完成本家族葬礼的唱诵,而不可能具备对史诗全方位掌握、唱诵的能耐。甚至也不需要练就这种功夫。在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从来都有两种思潮,两种方式,即泥古不变与推陈出新。陈兴华是后者。他突破祖训,投拜了三位师父。于是,他的史诗传唱之路就不局限于一个家族,变得丰富、悠远,海阔天空。正因为他三投名师,也才能积累起这么包容各家的、丰富的诗行。这是他在学习方式上独特的、创新的硕果。
怎么传承?按老祖宗的规矩,《亚鲁王》就是随着东郎的唱诵而传下来的,先辈们从来目不识丁,却把它完完整整地传承至今,史诗指引着苗人生前身后的无尽岁月。陈兴华也曾经是这样,但他内心深处又悸动着,不甘于仅仅是这样。为此,他不仅用传统的方式下苦功硬记,还跟一位识字的师父悄悄学习用汉字记苗音。而师父当年的这种做法也是躲躲藏藏的,在正式唱诵的场合,生怕被别人笑话而不敢公开。汉字记苗音,在陈兴华的《亚鲁王》史诗传承的路上,迈出了令人惊诧的一大步。因为陈兴华要破除传承道路上的旧习惯旧观念提笔记音;而限于小学一年级的汉文化水平,他更要越过认识汉字的一关。单就汉字记音这件事,就让我看到了陈兴华顽强的毅力和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的心态。这也是他迈向成功之路的法宝之一。
在“文革”期间,麻山不通公路,只能跋山涉水前往。家住县城的干部们都畏怯麻山。陈兴华在县粮食局工作,却总是主动要求上麻山。谁能琢磨透他的心思呢?原来,在县城及其周边,亚鲁王已被全面禁唱;而只要下去,他就可以在“山高皇帝远”的麻山避过风头,悄悄为人唱诵了。他有时甚至是白天在粮食局上班,晚上不眠不休地赶去乡间为丧家私下唱诵。他说:“那时,我的行动异常,曾经不知说了多少次假话,一些同事也都看在眼里,假装不知,不但没揭露我的这些事,反而给我很高的评价,得到局机关内独一的‘三优’称号……”
陈兴华版本的一个特点,是五言体诗歌。按他自己的说法,《亚鲁王》史诗百分之八十都是五言。用五言来唱诵比较好记,朗朗上口便于传承。中国社科院的吴晓东研究员说:“我在访谈陈兴华的几天里,几次遇到他的徒弟从河南、宁夏等外地打长途电话来询问译本中的某些句子该怎么唱。他的徒弟大多在外地打工,身边带着他这个只有汉文意译的译本初稿,以及相应的苗语录音。在看到陈兴华接他徒弟给他打来的电话之后,我相信他的这个译本正在起着传承的作用,虽然译本尚未出版。”但我们翻开中华书局版本的《亚鲁王》,其中有大量的篇幅是来自陈兴华的唱诵,书中有苗汉文对照的直译,却都是长短句,几乎没有五言体,这该怎么解释?有懂苗语中部方言的专家请他将另一首由他整理为五言体的婚姻古歌一句句地唱诵,专家在旁记数。他选唱的段落是八个音节,而其主干是五言,最后的三个音节要重复着再唱一遍。这个问题还有待苗语专家进一步的研究。
2012年陈兴华被评选为国家级传承人之后,更是凭自己的记忆,花四年时间把自己会唱的三万八千行史诗记录整理出来,又自己学习电脑打字,打印成册。这也许是非遗国家级传承人当中的唯一。当然,他的继承创新还是步履蹒跚,有些瞻前顾后。凭借他的精神和能力,在传承方式上,他还能再觅新径的。
在年过古稀之时,他和后生小伙们一道走进了亚鲁王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杨正江办的苗文培训班,成为最年长的、最用功的学生。陈兴华因为强烈的使命感和其开放的心态,因为好学,就能够比别的东郎在传承史诗的道路上多走一程。
四年推陈出新
三万八千行
余未人

吴晓东在和东郎交流
从2012年到2015年,陈兴华花了四年时间,根据自己的所学,翻译整理出了一个《亚鲁王》译本。陈兴华是史诗《亚鲁王》国家级传承人,他的译本是一个艺人译本,艺人自己翻译整理的译本目前鲜有出现,有其独特的价值。
应余未人老师的邀请,我曾就这个译本的出世、内容等问题,专程到贵州紫云对陈兴华做过三天的访谈。
以前我们看到的史诗文本,几乎都是由非艺人的学者或相关人员来完成的。艺人自己进行翻译整理,自然又有其自己的出发点。陈兴华说,他的这个译本最初目的是为了传承,也就是说,这个译本是要回到民间的,徒弟通过这个译本来帮助记忆,最后要在仪式中运用。
我在访谈陈兴华的几天里,几次遇到他的徒弟从河南、宁夏等外地打长途电话来询问译本中的某些句子该怎么唱。他的徒弟大多在外地打工,身边带着他这个只有汉文意译的译本初稿,以及相应的苗语录音。在看到陈兴华接他徒弟给他打来的电话之后,我相信他的这个译本正在起着传承的作用,虽然译本尚未出版。
文本要回到民间,而不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史诗的长度或别的什么,那么文本就会与其生存语境紧紧相连。换言之,《亚鲁王》是在麻山地区的丧葬仪式中演唱的,文本也就应该与当地的丧葬仪式结合在一起,这样,徒弟才知道在某一仪式环节该怎么唱。
陈兴华说,东郎会根据每次丧葬仪式中的具体情况来安排自己的演唱,比如说,演唱必须在规定的发丧时间之前唱完,时间紧的时候,就会只演唱主要的枝干。陈兴华的这个译本并不是根据自己在某次丧葬仪式的实际演唱翻译整理的,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所储备的内容翻译整理的。陈兴华在学艺期间曾经拜过三次师,先后跟随三位师傅学习,而且其中一位师傅还不同姓,在某些内容上会与本姓师傅有所差别,那么,可以说,陈兴华所能唱的内容,实际上是他师傅们所能唱内容的综合。他的这个写本,试图把所学到的所有内容都呈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这个译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综合本”,结合以上的实际情况看,这种综合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合理性。 在少数民族史诗的翻译整理方式中,通常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只有汉文意译,第二种是有意译与民族文字的原文,第三种是有意译、直译与原文,第四种是有意译、直译、国际音标与原文。提供的信息越多,越利于学术研究,只是采用何种方式,往往由多种因素决定。陈兴华的这个写本,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希望能提供苗文的信息,另外,为了更好传承,回到民间,提供苗文显得更为重要,但由于篇幅庞大等原因,最后只能单独以汉文意译的方式呈现,也是一种遗憾。
回到民间仪式
唱史诗文本
吴晓东


紫云东郎唱诵活动
后非遗时代的《亚鲁王》史诗传承
提问: 唐娜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回答: 陈兴华 苗族史诗《亚鲁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唐娜:听说您教徒弟用的方法跟原来不同了?
陈兴华:是。我们那个时候一句一句跟着师傅唱,要脑子记下来,实在困难的地方用汉语近音记录,记录下来的本子只有自己能看懂。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就记不下来。现在我对我的徒弟说,你们不用背了,大家年纪都不小了,如果拿起书能唱,就可以了。我们从前有规定是,老师怎么教,徒弟怎么唱。
唐娜:这些是新一批的徒弟吗?您之前没有四大寨的徒弟。
陈兴华:我2012年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以后,就公开招徒弟了。现在有多少新的徒弟我都不清楚,假如你一招呼,可能来三四十人。徒弟们来找我,给我录音录像,我就把录音给他们去听。
唐娜:他们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为什么来找您学?
陈兴华:大都三十岁、四十岁这批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也看到我成了国家传承人,觉得国家都重视了,他们也应该主动。他们懂得自己是苗人,必须要知道亚鲁王的故事,就是太难学了,一直回避。
唐娜:您是把书稿发给徒弟们让他们学习吗?
陈兴华:是的,2013年我就开始做这本书,到现在改了六稿。
唐娜:您不需要有负担,国家给你钱,就是让你减轻生活的负担,拿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做传承工作,不是要求您一分一毛地用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过去的方法行不通?
陈兴华:老的传统现在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情况,为了生活大家都要出去打工,生活好了人也改变了。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集中到师傅家里,蹲在火塘边来学,晚上就睡在火塘边,没有盖的,大家就烤背火。
所以我觉得按照传统的传习方式不行,要改变。什么措施都没有办法,只有写成书交给他,他到浙江、宁夏、广东去打工,拿起书读,拿录音听,就可以学。如果他有什么疑难,就打电话来问我。我一直强调:“在懂我的话的基础上,一定变成你们的话,如果不懂我的话,跟我多交流”。
唐娜:您哪些徒弟得到书了?
陈兴华:像得书的这些我比较熟悉,现在我送出十多本书了,这些人我是叫得上名字的。已经出师的这个叫伍兴志,还有韦应轮、韦朝学、陈小安、陈仕清、陈仕昌、陈仕文、伍小毛、韦国清、伍小宁、陈小富。
唐娜:您给书的人要达到什么条件?
陈兴华: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要学,我才给他。他不是认真想学的我不给,他想拿去试一下的我不给。
唐娜:这些人都在外面打工吗?
陈兴华:是的,有些没怎么见过面,我把书给他,把录音给他。他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来问,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唱给他,他说已经录音得了,真是太好了。我有一个录音笔,有演示的时候我就录下来,他们有U盘来拷去,现在形式多种。
唐娜:这是他第一次在葬礼上唱吗?
陈兴华:是的。我去安排的,主要去听他唱的。主人家请他回来的,主人家知道他有这方面知识,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我就打电话问他,他说他有把握。他把唱诵的录音给主人家,主人家先拿录音给我听,我认为确实还可以。我说交权给你,你可以唱了。
唐娜:他是专门为了葬礼回来的吗?
陈兴华:是的,他唱完第二天就回去了。他的录音我都录下来了。给他计算时间,一共5个小时55分钟。他还是很紧张,满头大汗的,我鼓励他说,第一次这样就可以了。
唐娜:听别的东郎唱,对您有帮助吗?
陈兴华:有。我听到好的部分,我就记下来。几千年来这个东西没有文字根据,也许我会的他不会,他会的我不会。有的人唱的少,但是他唱的内容我没有。
唐娜:既然老话是这样说,那么东郎自古以来究竟是不是受人尊敬的呢?成天顾别人家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东郎确实不是“聪明”的人。但是,如果一个家族没有东郎,也会被人嘲笑。
陈兴华:是的,也是不行。大家都觉得很重要,但是都互相推。像我现在一声喊,个个都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东西很重要,是民族的历史,有为人之道的知识,我要带头来学,但并不是抱着我要当一个东郎的想法来的。像伍兴志那样是真正想当东郎的,但是占的比重太少了。
唐娜:是不是普通年轻人听不懂了?
陈兴华:是这样的。我从小就崇拜这个东西,那时候老年人把去学唱《亚鲁王》叫做去学说话。按照老年人的说法,我们现在是不会说话的,不但没把汉话说好,连苗话也说得很不好。他们的语言特别美,该夸张的时候形容得特别好,现在我还听得懂,但大部分的人已经听不懂了。他说一句话,你就知道当时的场景,语言很生动。比如走路的样子,当时的气氛,一说就说出来了,但是你无法翻译成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