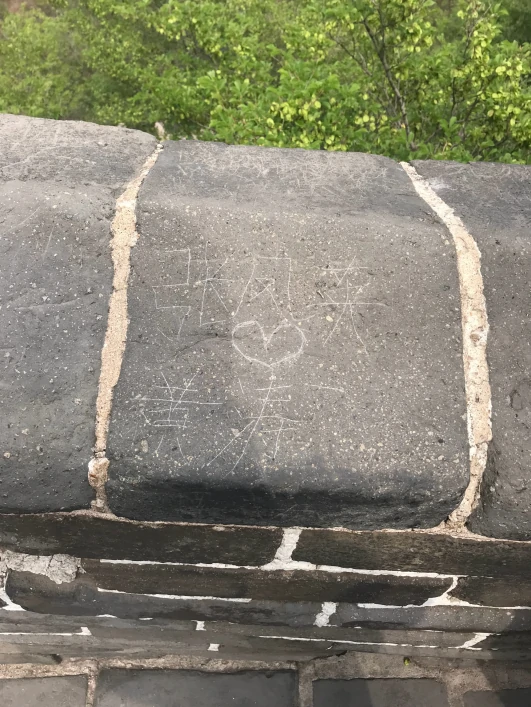小果:我渴望自由,在工厂被管怕了
我学习成绩不好,不想读书,十六岁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两年多都没有回去。开始是和二姐蓓蓓一起,后来二姐回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深圳,她走了几个月后,我就到了广州。
我最先去的城市是深圳。2004年到深圳后,去过电子厂、钟表厂、鞋厂。第一次去电子厂,做了一年零几个月,工资最高的一次是800多,平时一般500―700之间,有的时候还拿300,拿300的时候,一般是不赶货,也就是不加班的时候。
2005年,第二次进厂,是做收音机的机芯,平时一般800―900,工作环境好一些,加班的时候能拿1000多。做长了就乏味,这个厂对技术要求不高,只要能按规定做好要求的事就可以了,产品既销国内也出口。
第三次到了黄埔,在美盈鞋厂,和周婕在一起。打工三年,没有存多少钱,在外面开销太大,第一年和蓓蓓姐姐寄了一万块钱回家,后来每年能寄几千块钱回去。大姐小敏、妹妹媛媛、弟弟小招在家里读书,都要花钱的。后来我和蓓蓓姐姐分开了,消费就高了,就寄少了一点,我的日常开销主要是用在衣服上,衣服一般就几十块钱一件。蕾蕾姐姐没有和我们一起出来,她主要待在武汉,在制衣厂,和幺幺(小姑)离得近些。
我刚刚出来没多久时,特别想家,一想到回家就禁不住要哭,很想妈妈,但工厂里面总是不准假,要回家就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只得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就慢慢习惯了。由于车费贵,人多,过年回去不方便,在路上又累,怕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都是跟姐姐一起过。
过年时,工厂里人也不是很多。等熬到今年请了假,没想到2006年7月15日,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台风,只得放弃。
2004年在电子厂打工时,经常用有毒的“天拿水”。有些清洗工用乙丙醇清洗机器,他们也知道有毒,还是直接用手碰,整天都泡在那个水里,用浸在水里的棉签去清洗机器,不戴手套,厂里好像也没发手套。
工厂里没有好玩的事,也没听说有稀奇古怪的事。有一天,听说厂里一个经理上吊了,我们感觉很奇怪,后来才得知,总经理总是问他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随后总经理叫他辞职,他感觉没面子不想走,有一天喝完酒回来,就自杀了。关于他的死,现在还是个谜案,不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经理有三个儿子,听说他老爸也开了一家工厂,他真是太想不开了。不过在工厂干活,确实很累,真的很累,谁都不想干了。
厂里经常有工伤,很多人的手指“咔”的一声就没有了。不过幸亏我干的活不需要直接碰到机器,主要就是负责点数。我们车间也有气味,但也没人戴口罩,我们也不知道有毒。工厂噪音特别大,但没发耳塞,就算应付检查时发一下,事后也要收回去。
在电子厂,我一般一个月拿700块钱,有时要工作16个小时,晚上十二点下班,早上八点钟上班,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厂里。工作时间长,睡眠时间根本不足,每天就是吃饭、上班两件事。如果没有按时上班,就会被骂死,那个厂一般都是蛮赶货的,不能请假。
在厂里,最让人难受的是工厂规定员工不准挂蚊帐,也根本没有办法挂蚊帐,但广东一带蚊子很多。厂里没人管后勤,也没人管工人的利益,员工也懒得反映,觉得反映了也没什么用,也不知道和谁反映。
2005年,我换了一家工厂,到深圳一家钟表厂焊机芯。我记得焊锡放出来的烟好臭,工厂好像有吸烟的机器,可以将烟吸过去,但有时烟太大,机器不管用。有些人开始不知道可以用机器吸,也没有人教他们,烟都喷到脸上了。我开始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机器可以吸烟,后来看到别人去吸,才学着用吸烟机。
工厂的工作根本不用培训,很简单,只要是个人都可以上班。钟表厂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一般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700块钱,中间若稍稍偷闲了一点,就会被骂死。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中间可以休息一个多小时,一般按二十二天算,另外八天就算是加班。感觉一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吃饭、上班。厂里的伙食,天天萝卜白菜,青菜就是白菜,也有一点点肉,但肉量很少,早餐吃稀饭和包子,天天如此。
我没有留在电子厂,我好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做不长,待久了就会烦,就想要离开。我觉得换一下环境也不错,可以多学一些东西,多见一些世面。
两年了,我胆子好像大了一些,话也多了一些。以前妈妈总是担心我不爱说话,有一次过年,还特地把我送到城里的四姨家,让我去玩,和表妹们在一起。我在工厂也有一些好朋友,现在分开了,她们好像都没有离开工厂。我一般喜欢跟单纯、年纪小的女孩交往,不喜欢跟城府深的女孩来往,好像随时都会上她们当似的,感觉心累。
按规定,工厂一个月可以放一天假,但我来这个厂两个月了,都没放过一天假。我休息过一天,但不是放假,主要是因为赶货,我前一天通宵加班。尽管厂里董事长规定礼拜天晚上不准加班,但是一赶货,礼拜天晚上照样加班。有的人胆子比较大,不来,要是赶货不是特别紧,有一两个人不来也没什么,要是赶货特别紧,线长就会狠狠地骂人。我劳动的付出,肯定不止现在的工资,我的加班费太少了,一小时才一块五毛钱,深圳那边要高一点,一小时有五块。
2006年,我又换了一家工厂,离开深圳来到广州黄埔,进了美盈鞋厂,和周婕姐姐在一起。在鞋厂做工的时候,要黏胶水,厂里通风不好,鞋厂气味很大,但工厂也没发口罩给我们。
按照规定,在工厂上班时,是要戴耳塞的,但是厂里没有发,大家也不要求戴。也许习惯了那个噪音,感觉就会好一些。和深圳那家电子厂一样,每到要检查的时候,厂里就会把耳塞发给员工,检查一结束,就收上去了。
工厂发生了一些事情,瞒着不报,每次听说上面要派人来检查,工厂就将员工集合起来,每人发一张表格,给出要回答问题的答案,要求我们将答案背熟,如果不按表格提供的答案回答,就会受到处罚。奇怪的是,每次听说上面要来人检查,可是我从来没有碰上检查的人。
我感觉没有人愿意很认真地干活,员工和老板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立关系。在鞋厂,很多人将车间的原材料(比如牛皮)拿出来,其实这种损失是无形的,老板如果能够对员工好一点,他们也不会这样。
我感觉大家都挺冷漠、自私,好像不自私就会吃亏,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更是这样。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每个厂都会死人,有了病也没人管,工厂也不给他们请假,于是只好忍着。其实有些病根本就不是大病,而是身体太累了,身心疲惫,得不到休息。
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计件工资都是瞎算的,有的人到处玩和混,拿的工资比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多得多。我的工资是配合我开机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因为他比我辛苦得多。我是管点数的,我一般不会多点数,因为后一个程序还有品检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品检的人搞好关系,让他们把我的产品多算一些。
厂里管我们的人,好像是大学毕业生,从农村考出来的,骂起人来比较厉害,他的上级骂他,他就骂我们,我们也会骂他。做管理的人,一般靠关系进去,有的靠老乡关系,还有的靠一些当官的弄进去。有时候,我们厂还要帮别的厂做些事。
周婕姐姐主要检查鞋子的质量,工作要轻松一些,拿的工资也少一点。我和周婕住一层楼,但很少见面。周婕喜欢看电视,但厂里连电视都没有,只得跑到厂外面的一个小店去看,那里经常很多人。一般吃完晚饭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有个台刚好在五点半到六点半时段放连续剧,周婕就会跑过去,一天看一集。这个时候她看得正入迷,自然不好找她说话,等到下班,一般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有时还要到十二点或者更晚,这时候,大家都筋疲力尽,也不想说话,所以看起来和周婕住一层楼很方便,但实际上和她说话的机会很少。
我蛮喜欢做生意,喜欢做生意是渴望自由,我在工厂被管怕了。
振声: 建筑业倒了,我们就没饭吃了
振声是第三代已成年的三个男孩中,唯一没有念大学的孩子,也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孩子。
1997年,哥哥在四姐夫的食堂干活,忙不过来,便将留守家中的嫂子也叫去了北京,开始了夫妻同时外出的打工生涯。两个孩子则托付给了老人,当时,儿子振声七岁,女儿时春四岁。
直到2008年,因为四姐夫的工地出现问题,夫妻俩才陆续回到家中,儿子已经十八,女儿十五。振声勉强混完初中,在哥哥的强烈要求下,上了两年职校,学习数控。职校毕业后,在武汉妹夫的安排下,去了杭州一家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打工生涯。从老家到杭州,辗转多次,他终究无法在工厂立足,最后还是回到父辈的老行当,当了一个泥瓦匠。
我第一次看到振声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父母都在北京工地打工,只有每年春节时,才能和父母见面,一家人得以团聚。从七岁开始,振声和妹妹一起,与祖辈生活在村中,成为典型的留守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在哥哥、嫂子的描述中,振声是一个叛逆、倔强、不懂事的孩子,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脾气暴躁异常,更不懂得节约。
2014年,通过手机QQ聊天,振声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在父母和亲人的张罗下,仅仅几个月就从单身走向了婚姻。
今年过年回家,问到他打工几年的经历,才发现振声并不如嫂子叙述中那么幼稚、简单,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二代,振声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常人没有经历的苦楚,也面临很多只有他们这一代才能体会的困惑。
在父辈眼中,他不懂事的烙印也许难以祛除,但在我眼中,他身上也具备很多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素质。
时代在变,获取信息的方式在变,伴随而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唯一不变的是 父辈沿袭下来的农民身份。在现有条件下,父辈有限的能力,自然无法给振声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个体的成长,伴随着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很多阵痛。

姊妹们的孩子们2006年合影
爸爸妈妈去北京时,我七岁,妹妹四岁,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当时身体还好,但毕竟是老人,管不住我们,当时奶奶最担心我们出事,要求挺严。
妹妹学习不好,总是留级,念了好几个一年级,但她能说会道,在村里名气很大,明明自己读书不行,还说老师不行,给老师取外号叫“喷粪机”。
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念初中时,班上没有学习风气,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事情。课堂上,想听课的就听课,不想听课的就打牌,或者走来走去,反正念了书出来,也是打工,当时大家都这么想。
到初三时,我每次测验成绩都不是很好,就放弃了好好读书的念头,上学就在教室里混日子,反正就是混,总认为拿个毕业证就行了。老师拿我没办法,家里人也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叔叔挺希望我念书,像他那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我成绩不好。
随着我和妹妹长大,爸爸妈妈不在家,奶奶越来越难管住我俩。我们整天和她斗智斗勇,奶奶叫我和妹妹去捡棉花,可憋在棉田里实在太热了,人都透不过气来。第二年,为了逃避捡棉花的农活,我和妹妹趁棉花刚长出来,偷偷跑到地里,将棉花全部扯了。当时家里没有种田,农田一部分承包给了别人,一部分被村里统一承包给了老板,其实没有太多的农活干。奶奶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了饭就去上学,天天都是如此。奶奶喜欢喂鸡,家里到处都是母鸡、公鸡,我们吃了很多鸡蛋和鸡肉。
那时,整个村里只有一部电话,爸爸妈妈打电话来,我们就接;不打电话来,我们就不联系,一般一个星期来一次电话。为了方便联系,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表现情况、是否听话。我们在电话里提要求,提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他们回家时多带好吃的回来。事实上,因为每次回家都是春运,行李不好拿,火车也不好坐,爸爸妈妈从没有从北京带吃的回来,都是回来以后,带我们到集市上买。
我从来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我记得十八九岁那年,有一次,老爸跟我发了很大的火,我说他们整天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丢下我们在家也不管,大概是当时我的话触到了老爸的痛处,他就骂我,说你到时候出去就知道了。我当时也不懂事,想着他们在大城市,毕竟比农村好,但没想到,农村人到大城市,比家里过得还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