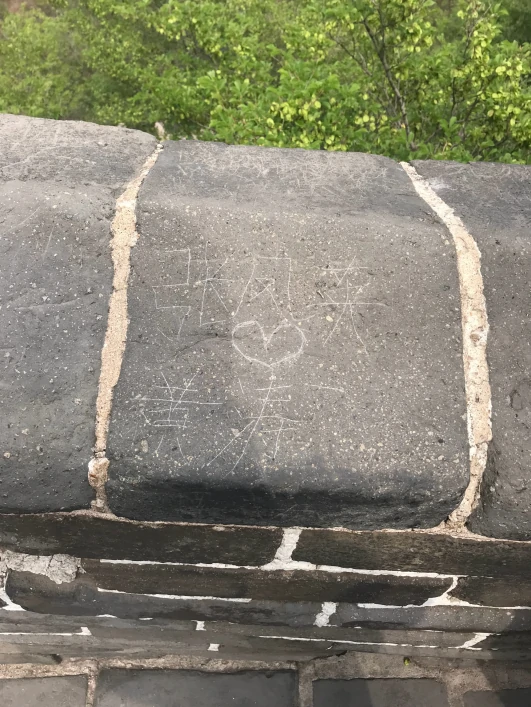赛来塘上的青春是充满骚动的。
我说的骚动指的是1996年前后的那些春天,从正青春的少年心里萌发出来的气息,与盛开在山坡河谷中的野丁香、一群群从容不迫的牦牛在赛来塘砂石街上留下的黑色花朵般的牛粪味合在一起,形成那个季节中某种暧昧的气味,在空中弥漫。
赛来塘很小,小到只有这一条砂石大街,还兼当着227国道,穿城而过,一路通往四川。不宽,双向单车道,由于地势原因,笔直的大街在文化馆前突然来了一个90度急转弯,拐向一个大坡后继续向前伸,直到玛尔柯河边,街尾杵着一个冷冷清清农机厂。
那时候,父亲看中了农机厂围墙外临公路的死角,准备在那开个饭店,厨师是他的本行。
等到年初,我就和父亲花了三天时间,整平了一块二十平米左右、漂浮着动物腥臭的地面,还作了硬化处理,又从王柔林区拉来不少松木板皮,搭成一个简易板房,最后,父亲用一块很大的蓝底白布条,镶嵌上“骑士酒馆”四个字作为酒�,挂在数米高的白杨树上。
1
文化馆的张二井常来“骑士酒馆”吃饭,每次来总是背着在当时还很少见的吉他,在等待饭菜上桌前就低着头一直弹,连个调都找不到。
“你就别弹了,这琴声比杀牦牛时的哀嚎都难听。”我说。
“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我非要学会不可。”他低着被长发淹没了的整张脸庞,缩着瘦弱的身体,继续宰牛般地弹着琴,“我要成为赛来塘第一个吉他高手。”
喝了二两青稞酒,吃完饭,张二井踉踉跄跄地走回文化馆。他应该算是赛来塘最早的文艺青年了,风吹长发,浪荡潇洒。这时正好老熊从玛尔柯河边坡底走了过来,看着他的背影问我,“他谁呀,狂呗!”
老熊全名熊能清,20岁,剽悍阴煞,满脸络腮胡,眼睛却女孩似的杏儿圆,是赛来塘养路段的养路工,平常总穿着洗白了的帆布小翻领工人装,裤子是大喇叭口,脚上套着双小白球鞋。
据同是养路工的老洪叔说,两年前,老熊在西宁马坊初中都没毕业,因打架斗殴调戏女同学,曾被短暂劳教过,后来,家里人想方设法把他送进达日养路段当养路工,刚去三个月,老熊就和当地的混混陈老六约了四次架,第五次的时候,两边虽都有帮手,但主要还是他俩拳脚相对,打到最后,老熊凭着事先藏在怀里的两把小号菜刀,硬是在自己负伤后把老六的后背上划了个血淋淋的X,疼得老六昏迷不醒才算是服了输。
那一次连公安都出动了,一个进了医院一个进了派出所。
养路段本是要开除他的,还是他家里人求爷爷告奶奶费尽心机托人走关系才算保住公职,不过却从达日调到赛来塘养路段。
也正是这场斗殴,让他在沿227公路线各养路段里的混混中名声大噪。
2
老熊调到赛来塘段后,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越发趾高气昂,领着从西宁招来的五六个年轻人,没事找事,打狗斗鸡,只要被他“看不惯”的人,都会去给人“上上课”。
老熊刚到赛来塘的第一个月,某天晚上看电影时,当地小痞子刘三毛在开演后才摇晃着进来找座位,挡了老熊视线好一会。老熊开口骂刘三毛,刘三毛回骂,被老熊立马挥拳打了过去。
听说刘三毛当时就说句,妈的敢动手,你给老子出来说话。二人就在影剧院前打了起来,刘三毛毕竟是这小地方的人,没太多打架经验,被心狠手辣的老熊打断了鼻梁。
赛来塘养路段准备将他退回达日养路段,但老熊也学聪明了,赶忙去找领导写保证书,说今后绝不打架斗殴,才被单位放了一马。
我深知老熊其人其事,知道其蛮干阴狠,见他问我张二井是何人,便低声说,“他有啥狂的,文化馆的小文人能比你还狂?别球理他。”
我想息事宁人,不料他反说,“操!在赛来塘的人,只要老子看着牛x哄哄的,哪天都会给他上上课……”
我心想张二井有麻烦了,得提早给他打个招呼,不要让老熊给欺负了。
 张二井看着是拒绝不了,还真把老熊收为徒弟了。
张二井看着是拒绝不了,还真把老熊收为徒弟了。
我还没来得及跟张二井打招呼,第四天中午,张二井一如既往地穿着得体的西装,文质彬彬地抱着吉他朝“骑士酒馆”走来。
问题是,上午十点多,老熊和养路段五六个西宁帮正在这里喝酒,到了中午,已经喝掉了二三瓶绵竹大曲了,正在兴头上。我赶紧出去截住张二井说,“今天你就不要来吃饭了,老熊他们正在找你的事呢。”
“怕他个球。”张二井直楞楞地就要里走。
老熊一伙正在店里兴高采烈的猜拳喝酒,等张二井一进去,立刻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看着张二井坐下来,反看着他们,情境竟有些窘迫。
“老板来个凉菜两瓶啤酒。”张二井喊道,然后像演奏家那样切翘二郎腿,抱起吉他弹了个流水音。
猛地,一声哄笑炸弹般地爆炸起来。老熊红着酒脸朝邻桌上的张二井说,“小子来一段?”
“凭啥?”他看着老熊说。
“操,让你来就来呗,问个球哩问。”
“我不卖唱,也不认识你。”
“好吧,今天让你认识一下。”老熊站起身来,朝张二井移动过来,其它几个也站起身来。老熊走到张二井的跟前用手拍了拍他的脸,这动作极轻佻,像早些年电影里恶霸地主调戏女人那样,结果被张二井用胳臂给拨开,老熊又敏捷地抓住了他的西装领,“操你妈的牛x得很呗,老子告诉你在赛来塘不要狂,别看你是赛来塘人,老子打的就是这种狂人。”说话间,老熊的脸上还是慈眉善目地似笑非笑,然后又补充一句,“你妈个x的。”
张二井本想忍下不吭声的,在听到第二次骂他,就火了。就在老熊放开他衣领时,顺手捡起凳子上的吉他猛地朝老熊头上砸去,“嗡”地一声,吉他在老熊头上轰响声中断成两截。
这突至的意外举动令老熊呆若木鸡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抬手去抚摸头顶,摸到了一块吉他的木屑,拿在手里看了眼才扔掉,好不容易回过神吼叫起来,“我操你妈你竟敢打老子?”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两个空酒瓶轮流朝张二井的脑袋上猛地砸去,张二井的头顿时血流如注,就势瘫软在凳子上。
我忙从旁边跑过来拉架,“何必大动干戈,都是县上的人,以后还要见面呢。”
老熊并不理会我的话,狠狠地朝张二井连踢了几脚,还往他身上吐了一口唾沫,便脚蹬着凳子,用袖子往小白鞋面上来回擦拭说,“把我的小白鞋给给弄脏了……”之后转身走到门口对我说,“我的饭钱让二井买了,他不买以后还打。”后面那几个小伙跟着发出浪荡的笑声。
3
我害怕张二井被打死出大事,忙伏下身把他扶在我的肩膀上,准备背他去医院,不料刚走到门口,张二井就迷迷糊糊的醒来了,一把推开我说,“我自己走,你把我的吉他保存好。”我愣在原地,看着他摇摇晃晃朝大坡方向走去。
不是冤家不碰头。过了半个月,张二井头上的绷带还没取掉,有天中午来吃拉面,老熊拿着从玛尔柯河滩里折来的一根极柔软有韧性的红柳条,像约好似的闪进门里。“哟喝,又碰上了!”然后直接走到张二井跟前,“吃的不错嘛。”
张二井没理会仍吃着拉面。老熊讨了个没趣,转了个圈后,又在张二井面前停住看着他说,“操你妈的不搭理我?”
张二井低头继续吃饭不吭声。老熊有点恼怒,挥起手中的红柳条朝张二井的头上抽去,被敏捷地用臂膊挡住了,老熊又抽,又挡,在老熊抽第三次时,张二井站起身来低声下气地对他说,“不要打了,我都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打啊?我从没惹过你呀……”
老熊听了仿佛更有兴致了似得,继续在张二井不防备时第四次抽了他,这次柳条稍正好抽到脸上,立刻有一道红色的肉岭凸现起来,张二井抚摸着脸颊,疼得倒抽了口气,有些哀怨地看着老熊。
“疼了吧!只要你求我,说被我抽疼了,我就不打了。”说着又抽一下,见张二井忍着还是没吭声,又说,“你真不疼吗?”。
“疼呀,要不我抽你一下试试。”
“那你为啥不喊哩?只要你求求我,我就不打你了。”老熊的口气倒像是求张二井似的。
“我从不求人。你愿打的话就把我打死算了。”
“口气硬得很呗。”说着又狠抽张二井一柳条,脸颊上又立刻冒出一条肉岭来,眼见着张二井眼里的泪就要流了下来了,但就是没流,噙在眼里来回转。
我实在看不下,走到老熊跟前说:“我求你放张二井一码,你今天的饭我请了。”
“你以为你有面子,去你妈个x的。老子打他关你啥事。当心揍你。”他用那双凶狠又好看的女孩眼睛瞪着我说。
张二井趁我们说话时想一走了之,但有俩人堵在门口不让他出,老熊转身从背后又猛抽张二井一下。“唉哟!”张二井这回是不由自主地疼得叫出了声,连脸色都变了,转过身来对老熊说,“何必呢,我们又不认识,你见我就打也不害怕我以后也这样报复你吗?”
“我是让你知道在赛来塘谁最牛逼。你不要狂,狂了还打。”
“好吧,你最牛逼,求你别打了……”
老熊一挥手中的柳条,对同伙说,“听到了吧,他说他求我不要再打他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没你的人情,是他自己争取的。”然后挥手让门口的人让开,张二井挤过那俩人出了门走到砂石路边,又踅摸回来,把头探进门里对老熊说,“我会记住你给我的羞辱……”
那伙人一听,全部轰地笑了。“羞辱”一词对这伙人来说过于文绉绉,可能他们还不明白那词真正的含意。老熊大声地对同伙们说,“他说我羞辱了他。”然后放肆地大笑起来。
4
这以后好多天,我都再没见到过张二井,有天文化馆的一个唱格萨尔王的评书家来酒馆吃饭,我趴在柜台上问他,“好久没见到张二井了?”
“他留职停薪去阿坝了,也许是都江堰,还有人说去了成都。”评书家含糊其辞地说道,“大概是背着那把断成了两截的吉他去学艺了。”他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
从此后,还真没再见过张二井,像是被玛尔柯河顺河的风刮走了关于他的一切消息。
到了1997年国庆节那几天,我陪父亲去玛尔柯河边钓鱼,意外地看到老熊带着他的西宁帮,和县长的儿子才让加也,以及另一帮藏族小伙在林子里打架。据说是老熊看不惯才让加在县上牛x哄哄的样子,到处勾引女孩,要给他上上课,反被才让加也给痛打了一顿。于是,双方便约定了这场斗殴。
西宁帮的那几个人不堪一击,一开始就被藏族小伙们打得落花流水,那帮藏族小伙挥着弯细的藏刀,蜂拥而上围着老熊一顿猛打,老熊一条胳膊被打折了,右脸颊上还留下一条三寸长的刀痕。
奇怪的是,这次打架,县公安并没有出面。老熊倒是从都到尾都没求饶一声,能打能挨就像个江湖英雄。
1998年,我和父亲把老“骑士酒馆”拆了,盖起了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还专门请文化馆的摄影师扎西达娃,把他花费数年拍摄的野生牦牛照片,以及当时那些歌星影星的相片,都镶嵌进相框里挂在墙上。
为了突出“骑士”这一特点,我还专门从西宁买来玩具飞镖,一排挂了三个在大厅正面的墙上。只要客人高兴,随时都可拿起飞镖随便扎上几下取乐。
秋天来了,赛来塘的秋天实际上就是初冬。
那天中午,我在砂石路边的酒幌下突然看见到有个熟悉的身影,背着吉他朝我走来,张二井回来了。我忙把他迎进门里,“这些年去哪了,连个消息都没有?”
“去青城山了!” 张二井喝了口我递过的茶,“就是都江堰那个武功盖世的青城山,学了‘青峰灯’。没黑没白苦学了三年,顺道把吉他也弹熟练了。承师傅恩准下山,现在回来了。”他没停地一气儿说完,还笑着对我说,“给你弹个‘爱的罗曼史’吧,让你见识下。”
然后他把有点粗壮的手指像蜻蜓点水似的,在吉他上优雅地划拉了一道,优美的乐声流泻开来,像水流汇成了湖泊。
湖水深深地淹没了他早已换成小平头的脑袋,原先洗得泛白的西装也换成了红色的夹克。就在他弹得尽兴时,老熊和养路段那几个人又�着进了酒馆。
真是狭路相逢。
5
我赶快起身招呼老熊往单间里走,可他根本不搭理我,直直走过去站在张二井背后。
“这是谁呀,他妈的弹得不错哦。”老熊往前走到张二井跟前,扭着脖子看着他,“哟嗬,这不是张二井吗,当年让我打的不知躲到哪去的小子又现身了,还弹琴?”说着还像以前那样伸手去拍张二井的脸,不料被张二井像钳子一样钳住了手,老熊不断发出“哎哎哎”的惨叫声,整个身体也随着张二井的手往上抬而扭曲起来。
“不要叫!”张二井吼了句,好半天才放开老熊。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飞镖玩具靶心,漫不经心地说,“你看清了,墙上左边第三个靶的八环。”说着松开老熊的手,拿起桌子上一支飞镖,一个漂亮的、如同京剧中武生亮相般的转身,“嗖”地一声,深深地扎在八环不到一厘米宽的黄道上。然后回头去看老熊,老熊眨巴着眼睛楞楞地看着。
见老熊不说话,张二井开口,“这三年没见你,并不是说我忘了你,刚才就是让你和这几个鸡巴熊孩子看看。”屋里安静得仿佛能听到一堆心脏高低不同的跳动声,空气中满是汽油燃烧般的炙热。
张二井盯着老熊的眼睛看了好一会,才转身走到我跟前,很客气地说,“老板哥哥,麻烦你拿着那个白酒杯站到窗台前伸开手。”我不知道他是啥意思,拿了个酒杯站定,张二井走到十米远外的墙跟,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个飞镖,斜着眼看了看老熊,说了声“走!”,话音示未落,只听得“�”的一声,我手中的小白酒杯像花儿一样在空中盛开,碎瓷片落了一地。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张二井你他妈的要老子的命呀!不要跟我开玩笑。”
张二井却满脸真诚,“对不起哥哥,让你当回模特,给那几个孙子开开眼。你们应该感谢老板。”张二井转头看了眼老熊一帮人,“替你们当了一回靶子。不过你要注意,说不定哪天你一个人的时候,飞镖就能扎进你的脑袋。”
“二井哥真厉害!啥时候学的这功夫?”老熊像是从楞症中调整过来,走到张二井面前,抖着声音毕恭毕敬地说。
“开始叫哥了?先别急着叫哩,知道这是啥吗?”张二井从口袋里掏出个棱形四边形发着青晕色的寒光铁片说,“这是真正的飞镖,可以致人死地!刚才飞的顶多叫玩具飞针。你看到那个长着大胡子的明星了吧,对,就是他。”他斜着眼示意老熊看墙上的海报,“你说要他哪只眼。”
老熊眨着眼半天没反应过来,张二井就慢慢走到老熊跟前,像老熊以前拍他的脸一样,拍了拍老熊煞白的脸。
“说呀!”张二井猛然有力地吼了声。
老熊像是被针刺了一下,浑身一颤结巴地脱口说,“左……左眼”,就在他话音落地时,飞镖犹如一道黑线,瞬间扎在了照片上人物的左眼位置上,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一屋人的脑袋整齐划一地随着飞镖转动,目光钉着飞镖扎在墙上画中人的左眼后,又回过头来默默地看着张二井,也看着老熊。
“要你左眼决不打你的右眼。”张二井兀自言语着,还是没人说一句话,整个酒馆的空气都凝固了一般。
“老板快给二井哥上菜,我请!”老熊突然献起殷勤来,笑着看着张二井,头上的汗珠哧溜哧溜地流个不停,他用手背抹了抹,甩甩手再往裤腿上抹了一把,回头看了眼同伙说,“快给二井哥倒茶呀,咋没点眼色!”几个同伙这才笨拙地跑前跑后,抢着要给二井递烟递水。
张二井像是没听见,也没理会弯腰递烟的人,径直往餐厅最里头,直到墙跟前,一转身,一道飞行物贴着老熊的额前就飞了过去,一枚寒光铁片直扎在门框边的木桩上,老熊“啊”的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
“打死人得偿命,我不打死你。”张二井笑着对老熊说。过了好久,老熊突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开始时是幽幽的,后面就开始大声嚎哭,像个孩子。
“你现在终于懂了啥叫羞辱了吧。”张二井站在瘫软在地上的老熊的旁边说,“你就这个熊样,你真叫我小看你好几眼。还硬装江湖人,除了打架还能干啥?”然后走过来重新坐在凳上,抱着吉他看着我说,“老板哥哥请原谅让你受惊了,我继续给你弹。”
“得饶人处且饶人,都是一个县上的人,打啥架呢,没意思……”我见形势好不容易恢复平和,赶快讨好张二井,“你这士别三日都成大师级了!”可他没接我的话,而是转头去看瘫软在地上的老熊,“哎,知道啥是‘爱的罗曼史’吗?”
音乐又开始响起,如同阳光洒在温柔安静的湖水上,屋里所有的空间都变得轻松起来。这也是我在赛来塘这个高原小镇上,第一次听吉他弹《爱的罗曼史》。
老熊慢慢地停止了哭泣,坐在地上静静的听着。那几个西宁帮的小伙或抬头观看,或坐在凳上默不做声,那乐声就像风,从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吹过。
6
就凭着这首《爱的罗曼史》,张二井开始在文化馆办吉他学习班,第一期竟在这弹丸之地上招了十个男女青年,到了第二期招生时,老熊第一个报了名,晚上还扛着一箱青稞酒到张二井的单身宿舍里,非要拜他为师,真诚到不收就要下跪。那箱青稞酒,按青海的风俗算是拜师礼。
张二井看着是拒绝不了,还真把老熊收为徒弟了。后来张二井来“骑士酒馆”吃拉面说起这事时,还表扬老熊在吉他上还是有点天分。
再后来,我再也没看到或听说过老熊和人打架斗殴的事。
2017年初,有一天我看CCTV纪录频道有六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叔带着把吉他一路玩到了云南大理,我总觉得里面有一人很像张二井,旁边还有个身材肥胖的男人,就像是老熊。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年男人们都是满脸沧桑,没有一点青春的痕迹,只在镜头前讲述自己对吉他演奏和行走的热爱,只字不提年轻时候。
算起来,张二井、老熊他们,如今也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