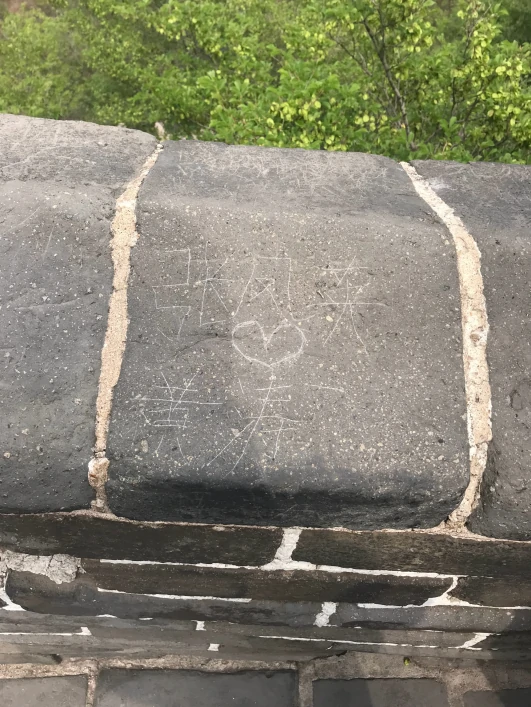1
1977年冬天,东营的天刚刚冷,妈妈便不断地往集上跑,但多是空手而归。三番五次之后,妈妈终于从集上扯回给我们做衣服的“蓝斜纹”。兄弟几个围着妈妈,一边争着看,一边不停地问:“有我的吗?”
“有,都有。”
“做几个口袋的?”
“几个都行。”
“明口袋,还是暗口袋?”
“愿意要啥样的,咱就做啥样的。”妈妈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
憧憬是甜蜜的,但等待却是一种煎熬。啥时候能穿上新衣裳?我们兄弟几个不断地琢磨。自从买回“蓝斜纹”,妈妈就忙碌不停,白天上坡干活,晚上扒下我们的衣服摊在“蓝斜纹”上,用磨尖的粉笔描样子,一边描一边自言自语:“多一指?还是多两指?”
妈妈的手向外斜着,画出的白线离衣服足有三指多,“大一点,能多穿一年。”妈妈像是在给自己一个解释。
前襟铰好了,后片铰好了,袖子也铰好了。妈妈在碎布片上剜出领子和口袋,找一根长一点的布条,一卷一卷地扎好。
小时候的年,就是从妈妈手中针线游走的那一刻开始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每晚在油灯下,边写作业边看着妈妈一针一线地缝衣服。
那天晚上,看着妈妈脸贴着针,针贴着豆粒大的油灯,就真的像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不知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等妈妈的眼熬红了,脸熏黑了,手不知被扎过多少次,终于在一天晚饭后,她让我们脱下旧衣服,试试新衣服,我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往自己身上穿。
“慢着点,别挣开了缝子!”妈妈一边喊,一边逐一整理我们的衣服,绾绾领子,拽拽袖子,满意地审视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兄弟仨兴奋地把到手插在口袋里,学着京剧老生,踱着方步,一拽一拽地在屋里转,仿佛明天就要过年了。
可就在我们意犹未尽之时,妈妈说:“脱下来吧!过年再穿。”我们这才极不情愿地脱下新衣,看着妈妈把它们叠得方方正正,一件件放进箱子里。
2
真正的年是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开始的。二十三是城里西关大集,大人孩子早早吃了饭,就成群结队往大集上赶。
集上的人摩肩接踵,集上的货琳琅满目。卖鱼的、卖肉的、卖菜的、卖布的、卖百货的占据着道路两边的位置,叫卖声此起彼伏。
最热闹的是鞭炮市。在“不响不要钱”的吆喝声中,一串串点燃的鞭炮被抛入半空中,“噼里啪啦”地招呼着过往的大人和孩子。
看着五颜六色鞭炮,孩子们的脚下生了根,任凭大人怎么拖拽与呵斥,一步也不肯挪了。大人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从一层层的衣服里摸出一张皱钞票,嘴上还不停地与小贩讨价还价。付了钱,搭上一句:“再送一支。”
“赔本了,送不着了!”小贩双手护住鞭炮,像怕被人抢了去。没有油水可赚,大人便牵了孩子往前走,边走边说:“你这个要钱鬼!”孩子却什么也有没听到,只顾着欣赏手中的几挂鞭炮,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
集市上,人们一份儿一份儿地问价钱,不时挑着物件的毛病,比量来,比量去,手中的钱始终攥得紧紧的。大集转了几遍,已是晌午,许多人还是两手空空。日头又向西斜了一竿子,小贩们就更加起劲地吆喝:“便宜了,快来买呀!”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
“买了年货,好回家辞灶!”
两手空空的人最终咬咬牙,买了。可手中提着东西,又不时盘算:“二十八的集,会便宜点吧!”
 集上的人摩肩接踵,集上的货琳琅满目。
集上的人摩肩接踵,集上的货琳琅满目。
回家时,已是日头西斜,错过的晌午饭也顾不得吃,一家人便忙着包饺子。
太阳没落,心急的孩子就开始点爆竹,左邻右舍的鞭炮声,陆陆续续地响成了一片。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与纸片燃烧的气味,年味也就有了。
一只只饺子像生气的河豚,在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翻滚着。第一碗舀出来做供样儿,是孝敬各路神仙的,谁也动不得;第二碗是给老人的;之后便没有什么讲究,孩子们停了说笑,甩开腮帮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小年的饺子,家家不同:殷实的人家,白面猪肉;一般的人家,白面素馅;日子过得紧巴的,一顿杂面饺子也算是过小年。
待我们的肚子鼓起来,嘴里哈着气,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妈妈不失时机的,变戏法般从身后拿出一个小纸包。
“啥?”
“猜!”
“猜不着。”
妈妈不再吊我们的胃口了,一层层揭开了纸。
“糖瓜!”我们一声惊呼,眼睛里放出光来。妈妈分糖瓜,一人一块,“这糖瓜是给灶王爷吃的,粘住他的嘴,到玉皇大帝那,光说好话不说坏话。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开始,我们一点点地舔,到最后实在拿不住了,才舍得放到嘴里慢慢嚼。糖瓜很甜也很黏,把牙都粘到一起了。我一边吃一边想:“灶王爷的嘴巴粘住了,坏话说不出来,好话怎么能说出来呢?”
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想明白。
3
过了小年,就真的开始过年了。
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为过大年做准备,一切都遵循着“廿三祭灶,廿四扫房,廿五做豆腐,廿六杀肥猪,廿七宰鸡,廿八蒸年糕,廿九白面发,三十贴对联,大年初一拜大年。”的老话,按部就班进行着。
在此其间,我们这群孩子们就一直围在大人身边,上蹿下跳,跑前跑后,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但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讨一口好吃的。
二十九的晚饭后,妈妈开始揉面蒸馒头,一年中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上手的机会。
妈妈极为大方地给我们一人一个面剂子。我�下一半,学着妈妈的样子在面板上用力的揉搓,先把面团捋成水滴形,用剪刀一排排地剪出三角形的刺,再找两粒绿豆,按在面团前部,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刺猬,就静静伏在面板上了。
另一半面剂子,我搓成长条,两头向里盘,压住面条。在每个面条头上各按上两粒绿豆,“圣虫”就做成了(“圣”通 “剩”、“升”之音,寓意来年粮食有剩余,日子步步高升)。
再想要个面团做点其他的,妈妈是断然不会允许了。等馒头一个个整齐地装在十印锅里,刺猬和圣虫也一并进了去,妈妈便盖上黑黢黢的�子,开始往灶里添柴禾。
小屋里的烟慢慢多起来,围着小油灯一缕缕的向上升腾,最后融在漆黑的房顶中。我们坐在暖暖的炕沿儿上,不安分的用脚后跟儿有节奏地敲打炕沿,盼望着�子上快点冒出热气。
渐渐地,敲击炕沿儿的声音小了,节奏乱了。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我们用力睁开眼睛,急急地说:“我不打盹!”说着便正襟危坐起来。
妈妈停了火,站起来捶捶腰,我们急急地问:“中了吗?”
“中了。”
“快掀锅吧!”
“稍跌一跌。”
在我们企盼,甚至略带乞求的眼神中,妈妈弯腰掀起了湿沉的�子。一股热气“腾”地填满了整个房子,妈妈不见了,我们不见了,只有那油灯的小火苗在热浪中左右摇摆。
馒头甜甜的麦香直往人鼻孔里钻,等热气散了,灯光仿佛亮了些,照在大黑铁锅里的馒头上,白晃晃的,闪人眼。白白胖胖的馒头一个紧挨着一个,静静卧着的圣虫也似乎似乎大了几岁,那两只小刺猬满身的刺都�挲开,小眼睛闪着绿光,就要动起来。
妈妈用大碗盛些凉水,把手蘸一蘸,小心翼翼的从锅里拾馒头,然后一个个整齐地放在面板上凉凉。刺猬不再那么烫手了,妈妈便递给我们,我们小心地把玩着,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案板上的那些馒头。
妈妈会意的一笑,拿起一个有嘎渣儿的不太俊俏的馒头,一掰两半放在我们的手里。
“快吃吧,小馋猫!”她又解释说:“这些好的,要留着待客。”
馒头拿在手里,我们先吃皮,再吃瓤,最后吃嘎渣儿。馒头绵软弹牙,嘎渣儿浓香焦脆。我们小口小口地吃,一层一层揭着吃,慢慢地嚼,慢慢地咽。
最后,在妈妈“天不早了”的催促中,我们搂着小刺猬,睡了。
4
年三十早上,我还沉浸在吃馒头的梦里,早饭却只有杂面卷子和地瓜汤。一家人匆匆吃完,便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
妈妈拉炉子,爸爸扎上包袱皮,我们有的拉风匣,有的裹面,有的端盘子拿笊篱,帮大人准备炸带鱼、炸藕合、炸扁豆。
炸出的食物黄灿灿的,放在一张粉皮儿上控油。每每炸出一样,妈妈就给每人分一点品尝,我总是忘了手中的活计,小心翼翼地吃着,用力把下嘴唇向上兜着,生怕掉一丁点在地上。
不一会夫,该炸的都炸完了,爸爸把粉皮儿上的鱼和藕合倒进盆里,然后把沾满油的粉皮儿放进油锅,“刺啦”一声,粉皮儿变得又白又厚。
捞出来,把油控干,再往盆里轻轻一放,粉皮儿立马四分五裂。大家围着盆子,拿起一块放在嘴里轻轻一咬,伴随着清脆的“咔嚓”声,带鱼、莲藕、扁豆的香味就在口中弥散开来。
一切收拾妥当,爸爸便在小饭桌上开始裁红纸、写对联。
我们压纸的压纸、研墨的研墨,随着爸爸的笔画,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不认识就猜,猜不出的就问。写好的对联摆在地上、桌子上、炕沿儿上晾干,到处都大红色。
中午的菜是用油渣炖的,放了白菜、粉条,还有冻豆腐,满满一大锅“咕嘟咕嘟”冒热气。吃饭前,妈妈说:“放圣虫啦!”
于是弟兄几个掀起盛粮食的瓮盖,妈妈拿着蒸好的圣虫埋到粮食里,一边埋一边虔诚的祈愿:“圣虫保佑,粮食越吃越多!圣虫保佑,天天都吃白馒头!”
一家人匆匆的吃饭,村东头陆陆续续传来鞭炮声,已经有些人家开始上坟祭祖了。
“快去吧!去晚了出懒汉!”奶奶催说。于是在爸爸的带领下,我们提包袱的,端圈盘的,拿酒拿鞭炮的,从家中一涌而出。
大街上已是人来人往,有往坟地走的,也有上完坟回家的,时不时的相互打招呼。坟地里挤满了人,大家纷纷跪在自家的坟前烧纸,由年长的人向祖先汇报家里一年的情况:“有吃有喝,吃不愁穿不愁,放宽心。就过年了,来给你送钱,使劲花!”
汇报完了,纸也快熄灭了,各种供样儿放一点,浇上酒,便开始放鞭炮。在鞭炮声中,在烟熏火燎中,在大人孩子的说笑中,平日坟地里恐怖的氛围荡然无存。
如有大家主请影,那就更热闹了。在村子边立起祖宗的牌位,方桌上摆着猪头、整鸡、鲜鱼和各色的时令果蔬,点起三柱高香。在族长的带领下,从耄耋老人到蹒跚学步的孩子,同祖同宗的男性一起行三叩九拜的大礼,请老爷老嬷回家过年。行完大礼,便敲鼓打锣、燃放鞭炮,比娶媳妇还要排场。

上完坟回到家里,妈妈已经开始剁馅,准备包饺子了。
在爸爸的招呼下,门里门外的大扫除也开始了。把院子里的杂七杂八、破破烂烂的东西归置归置,能摆的摆好,能藏的藏好,那些确实找不到一点用处的,便扔到小推车里,连带着扫出的碎纸、树叶和柴禾,一起推到村北的公路沟里。
家门前的大街上,像换了一片新天地,原本熟悉的院子和街道,这时似乎都变得有些陌生。到处干干净净,各家都在打浆子贴对联,一片红火。
懒汉们上坟的鞭炮声还没点燃,有的人家年三十吃饺子前的爆竹声已经响起。
天刚刚擦黑,爸爸点起嘎斯石灯,黑黢黢的小屋里一下子亮如白昼。天不早了,村南边的天上一闪一闪的亮着,县城里的鞭炮声一阵阵传来。一群半大小子、姑娘挤进我家,急头白脸的非要我爸爸拉呱不可。
爸爸没办法,就讲了一段《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孩子们还是不散伙,非要听鬼故事,爸爸又讲了《马王堆女尸》,绘声绘色,一群孩子听得一个个大气不敢出,脊梁沟里直冒凉气。故事听过了瘾,但却不敢回家了,妈妈只好打着灯笼,把他们一个个往家送。尽管害怕,他们第二天晚上还会再来。
妈妈送人回家时,外面就响起了交夜的鞭炮声。“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爸爸说:“新的一年到了,早睡吧!还要早起。”
我们向妈妈要了新衣服,整齐地放在枕头边,听着外面连成一片的鞭炮响,看着窗户纸上忽明忽暗的光亮,回味着爸爸讲的故事,脑袋不住地往被窝里钻。
5
年初一被妈妈喊醒,饺子已经端上桌了,我们也终于能穿新衣服了。
爸爸妈妈给坐在正座上的奶奶磕头。轮到我们给奶奶磕头,我们都说:“奶奶过年好!”“好!好!一家人噶都好!”奶奶高兴地答着,满脸的皱纹堆成了一朵花。
磕完头,赶紧吃饺子。吃着吃着,“嘎嘣”一声,爸爸硌着牙了。他从嘴了吐出一个硬币,放在桌上。
“恁爸爸有福气!”奶奶笑。
我们羡慕得不得了,用筷子在碗里不停地翻,妈妈连忙说:“就包了一个,都有福。”
正在我们为没有吃到钢�儿而有些失落时,院子里传来了吆喝声,“四婶子,过年好哇!”
拜年的人来了,一家人赶忙收拾了碗筷。妈妈负责在家照应客,爸爸就带我们出门拜年。大街上熙熙攘攘,大家都穿着新衣服在人缝中钻来钻去。
辈分高的、年长的,我们要一家家地串。还没进屋门,就要在天井里高声喊:“大爷、二叔,来给你拜年了!”进了门,便“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连磕三个响头,老人们连谦让的机会也没有。打头的长辈磕了,跟班的不管门里门外的都接连跪成一片。
老爷爷一边说着快起,一边给男人分烟;老奶奶端着笸箩,慷慨地给我们分花生,分糖。串的门子多了,我们也变得挑剔起来,有的便不再要,没有的就赶忙接过来装在口袋里。
大半个上午转下来,我们的口袋已经快装不下了。
初一中午的饭菜是一年中最丰盛的,有鸡、有鱼、有菜,大白馒头都可以放开吃。爸爸烫上一壶白酒,慢慢喝,惬意自在,菜却让我们吃了个底朝天。
饭后,还有陆续来串门的,这时就换爸爸招待了,妈妈和大娘要去给人家的老人拜年,“早晚不要紧,谁都知道这一天忙,礼是必须有的。”
生产队的场院上传来锣鼓声,是别村的玩玩意儿的来了。
我们连忙邀三喝五往场院里跑。是踩高跷的!有取经的师徒四人,有各路英雄、各路神仙,有解放军,有坏蛋、小丑和罗汉头。一大群人随着鼓点,在哨声的指挥下变换着队形,做着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中间休息时,“唐僧”和“猪八戒”竟然抽起烟来,我们好奇地围上去。胆大的伸手摸八戒的肚皮,八戒叼着烟卷,突然一晃手中的钉耙,一个鬼脸吓得我们惊呼四散。
6
初二走姥姥家,是很令人兴奋的事。
一是能和一群表兄弟玩。我妈妈姊妹五个,尽管那时四姨五姨还没结婚,但外甥们已经足有十来个。一大帮孩子涌进来,把姥姥家的小院挤得满满当当;二是有好吃的;最最重要的是,我能领到压岁钱。
舅舅吆喝着:“都来给姥爷、姥娘磕头!”
于是呼啦趴下一大片,卖力地磕头。姥爷说:“好啦好啦!都起来吧!”
“来来来,排好队!”舅舅举着手喊着。
外甥们从十几岁的到嗷嗷待哺的,都乖乖排好队,舅舅不管大小,一人发一张崭新的五角钱。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那是舅舅卖了一冬的蒜黄儿攒下的,为给外甥们发压岁钱,他特地到银行换了一张张新钱。
我们把钱装在口袋里,高兴得合不拢嘴,手不时地要摸一摸。二十多口子人聚在一起吃饭,男人一桌、女人一桌、孩子一桌。凳子不够,搬块砖头也凑合。
有一年,我和弟弟坐在一个放倒的杌子上,一不小心,身子向后一仰,“出溜”一声掉到了杌子的空隙里。摔一下不要紧,可双脚一撂,把盛菜的小桌掀翻了,碗碟“稀里哗啦”滚落一地。
妈妈呵斥我们,姨们一边劝说,一边把能吃的菜拾到盘子里,原本不多的菜已是所剩无几了。再做,不是时间来不及,而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做了。
大人就把菜给我们匀过来一些,我们诚惶诚恐地吃完饭,但很快就把自己闯祸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7
从初三开始,日子就是在走亲戚和待亲戚间来回循环,今天我到你家,明天你到我家。初五的早上放鞭、吃饺子,饭后妈妈就脱下我们沾满油渍和泥土的衣服,一一洗净,好留到我们开学的时候穿。
妈妈一边洗衣服,一边催促:“玩够了,该写作业了!”
“哪里玩够来?”我心里嘀咕着,看着自己身上老旧的衣服,极为不自在,更没有心思写作业了。往往写不了几行,便趁妈妈不注意,一溜烟窜到大街上,拉帮结伙的疯玩去了。
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飞快,很快就到正月十五了,作业不做是没法交差的。于是我硬着头皮开始写作业,有时急得抓耳挠腮,甚至难为得哭了起来。
可就算哭得再狠,父母也会不搭腔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自己胡乱对付,潦潦草草糊弄完作业,实在写不完,就早早计划着怎么应付老师。
正月十五就是正月十五,晚上放了最后一支鞭,吃过水饺,天明就要开学。年就过完了。
中午放学的路上,我还会遇上挎着筐子或是箢子走亲戚的人。于是想起过年,自己跟着爸妈走亲戚吃的好东西,不禁对这些还沉浸在过年氛围中的人,无比羡慕和嫉妒。
又煎熬了半个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妈妈把过年蒸糕时撙出来的糕面擀成棋子,再加上一把黄豆,分着炒熟,我们就有“蝎子”吃了。
到了春天,我撑着口袋,帮妈妈�粮食。一下子�出了年三十放进粮食堆里的圣虫。
面对久违了的面干粮,惊喜溢于言表。
可干透了的圣虫掰也掰不开、啃也啃不动,我只好闭起一只眼,用后槽牙奋力地咬下去,却也只能在圣虫身上,留下一对浅浅的牙印儿。
也好,意料之外得来的美食,要慢慢吮着吃。偶尔啃下一块来,细细地品一品,竟还带着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