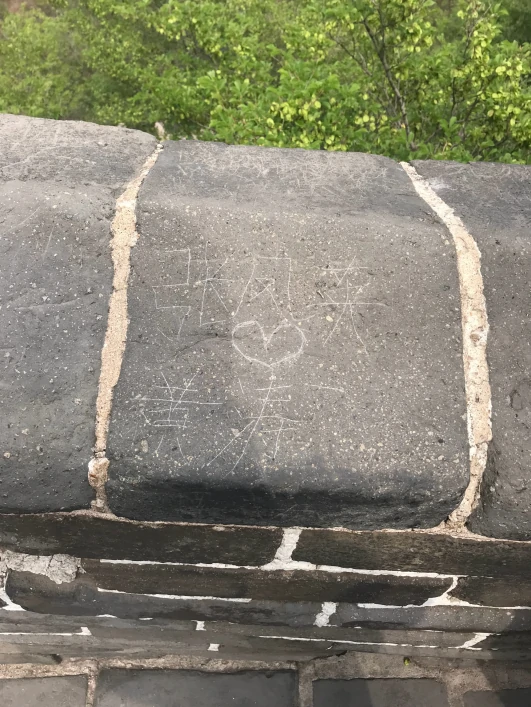他出现的时候文质彬彬、谦和质朴,没有那种户外大汉的吓人气势。他剪掉了长发,剔掉了胡子。他很瘦,你不知道他怎么能逃脱约三百斤的蟒蛇的猎捕。他眼里温柔,让人难以想像他被二十只狼围攻时的情景。
独行十年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记忆会一点一点消蚀。于是他住在昌平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纪念馆,那里塞满了流浪旷野的照片、生锈的腰刀、载重的独轮车、各地的县志、古生物化石、各种奖杯奖状、他自己的指甲盖和牙齿。
打开窗户,他能看到太行山脉在北京昌平沉入平原地区的最后一座山头。这里空气纯净清冽,山谷里的别墅刷成灰绿色和明黄色,在深秋天空下闪耀着平静和喜悦。他和新朋友在这里喝茶,他们想知道某一种人生是不是比其他的人生更好、更精彩、更宏伟。室内也没有那种普通生活的气氛,他的一年两个月大的儿子住在这里,儿子在襁�里睁大眼睛盯着一群陌生人,他们进来参观,挥手告别,走时还摸摸他的小鼻子说再见。回首时,看得到门边挂着一副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的金色牌子。
雷殿生一个人走了十年,他走丢了指甲盖,缓慢地超越苦痛;他钻出原始森林,走入了阿里无人区,缓慢地超越孤独;他三进罗布泊,把陨石放在独轮车上,又推车越过了秦岭,不知不觉超越了偶像余纯顺。他在中国狂行了十年,常常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大都市里进入夜生活时,他还得夜行数里,只为了找到一块2米长1米宽的平地来睡觉。他穿着一件90元的棉夹克,独自爬到了珠穆朗玛峰7000米高度……时间之久,路线之长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万水千山,都被这个人走遍了。可是,把生命里的十年都扔在柏油路、乡村小道、山羊跳过的峭壁、沙漠、沼泽和什么都没有的云雾里,到头来是一场空,这人到底要干嘛?
1
雷殿生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那个学期,他看到一套徐霞客的邮票,邮票告诉他有一种人是这么想的:要和别人不同,爱什么就干什么。
1989年,他在大庆图强火车站看到一个人,身材魁梧、满脸大胡子,背着小塔似的旅行包,包上裹着一张红布,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徒步全中国,上海---台湾。”
他在照片上见过这个人,拔脚追上这位大侠:“余纯顺老师……”
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有一个问题不敢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走?”他知道,这个问题一出口,大侠就觉得你是个傻子。
“你得把阑尾割了。“余纯顺对他说,“如果你要走。”
他记住了这个秘诀,去图强镇医院把阑尾割了。
他把九节鞭攥在手里在树林里挥舞,然后折叠起来放进口袋。他每天跑5公里,三个月后开始跑10公里。他买了十多种地图,从总图到分图绘制出一个完整的网络。他在书上学了很多医药知识。他学习如何用刀、止血、辨认方向、获取食物和水、应对滑坡和劫匪,如何用救生绳翻越悬崖。最重要的知识是,他如何攒下足够走十年的钱?
别人卖油条,他批发油条。别人6点开张,他5点就炸好了数千根油条,用塑料布裹着批发给自己的“经销商”。他自己制作洗衣粉,买来几桶化学材料,把它们兑在一起,洗衣粉是机器吹出来的,他用根棍自己搅。他把洗衣粉简装在大塑料袋里,低价拿下了村里村外的小市场。他到工地上做工,学了瓦工、电工和项目流程,摇身变成了承包商。他担上风险径自去谈项目,一个项目下来,破夹克里兜住几万块钱。在上世纪80年代,工人一个月不到200元,万元户就是那时的富豪。他算了算,自己一天就能赚1000元。
他不喜欢身边的环境。他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工地上好挣钱,但工地文化太粗糙,一伙人骂骂咧咧,海吹冒料。
1994年,他在北京国贸上班,这里据说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人们走路都没声,厕所香味扑鼻,空间里飘着金凯利的《回家》,女士们都丰胸翘臀。一晃四年过去,他的行囊塞满了,存折里有了几十万储蓄。他的身影出现在黑龙江102国道的端头。
 雷殿生(图片源自网络)
雷殿生(图片源自网络)
行囊重达100公斤。药装了6公斤、斧头、刀、春夏秋冬的衣服、食品、水、手电、收音机、相机、绳索……他走了一天就垮了。第二天,弟弟开着农用车追上他,卸下了30公斤。他回过头继续往前走。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把自己的全部家当:录音机、大摆钟、四头公猪、铁锅、农具和桌椅板凳都给了姑姑。剩下的70公斤就是他的全部,他从1998年一直走到了2008年。
他穿着一身红色的运动外套,嘴唇上留着胡须,瘦削的脸上架着近视眼镜,衣服里裹着把一尺长的腰刀。从哈尔滨南下,第一站去长春。在他的计划里,一天得步行10个小时。晚上他在路边僻静处扎好帐篷,在大地上结结实实睡一觉。蛐蛐在旁边欢唱着,他睡得很香。
他在水沟里洗脸,钻到白杨树丛里方便。他看到晨曦里的麦浪,听到群星下的江流呜咽,火车从他面前闪过,麻雀在头顶飞舞。他头发越来越长,浑身的气味越来越像个野人。他把鞋带松开,坐在石头上,大脚趾肿得像一块紫蛋挞,脚掌和五个脚趾上全是血泡。他打开收音机,天空里有无线电讯号,他听得到城里人拉扯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件。
他站起来再走,如果每天不走十个小时,十年就走不完地图上的路线。他沿着102国道的弧线走进华北平原,那里地形平坦、径陌罗织。走村过户时人们靠在门边瞧他。1998年,人们和自己的身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工人在城市,农民在农村,大家稀罕着这种哪都不属于的流浪汉,他对他们笑笑,他们赶紧走进门去。
下雨了,他去住5元钱的旅馆,但是身份证被退回来了,“不接待。”
“为什么?”
旅馆大妈不说话。
“我有身份证啊。”
“不接待。”
“不接待。”另一家旅馆大妈说。
“不接待。”其他旅馆大妈也这么说。
他把帐篷扎在雨地里,雨水从地上四面流来,他盘腿坐在水里,像一个佛。
很多人怕他,很多人厌恶他,还有很多人追着他看,他一回头,那些人就哄笑着跑开。他想去讨一杯凉水,尽量把话说得很温和,“您……”
“你出去,出去。”
他的头发太长了,胡子也太长了,他带着近视镜没有修正印象,反而有点奸滑。
“你别站在我家屋檐底下。”
他只想站在那里躲雨。
2
他哭了。继续走,走过平原,走到江南。“你为什么走啊?”人们就是想知道这个问题。他嘴唇紧闭。
他做着走遍中国的梦。他的快乐铺在大地上,树叶在春光里闪闪飞舞,聆听小鸟齐唱,走进一条林间的小路,坐在高山上看远方。
他知道自己将要走过珠穆朗玛峰,别人在那里登山,垂直运动。而他的水平运动覆盖了垂直运动。他知道自己将出入罗布泊,别人说那是生死考验,在他来说,他出发时就已经重生了,死在哪一段路上不是死?他踏遍名山胜水,别人说那是旅游,在他来说,那是回归,每处山水都是他的情人。他寻访民俗风情,别人说那是采风,在他来说,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在神农架的密林里。他在密林里找到了宿营地,支起帐篷。森林的黑暗无边无尽,但在一道闪电中纤毫毕现。接着成千上万的雷声炸开,滚落在身边,像是魔鬼在黑暗里厮杀。他第一次感到如此惊怕。大雨狂暴地撕扯着森林。闪电无数次击落在大地上,似乎要带走他的命才算完事。他等着,盘腿坐在透水的帐篷里,用记号笔在帐篷上写下:佛、佛、佛、佛,阿弥陀佛……
雨住了,夜晚结束。他抖落雨滴,头痛欲裂,继续穿越森林。
他在竹林小岗上遇到一只巨蟒,菱形花色的三角头有一只狗头那么大,眼睛黑如柏油。它的脖子细一些,但身子比头还粗,波浪状眩目地游动着。他跑了几步,回过头,掏出辣椒水,对着蟒蛇摇晃的大脑袋一喷,它吃惊地缩回去了。他用牙齿咬住鞭炮,颤抖着点着了引线,炮声拍击着山峦,巨蟒一下不见了。
在路上时,有时手机突然响起来,姐姐打电话来,“你在哪里?”
“雅鲁藏布江,在过绳索桥。”
“吊在绳索桥上?”
“嗯。”
“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7年。”
“别瞎逛了,回来吧。”
“我得走完。”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你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我听不见了!这边水声太大了!”
他来到一个市镇,会走进一家邮局,把一张白布展开请工作人员在上面盖一只邮戳。他和当地人拍照,邀请借宿的一家人拍个全家福。他站在家徒四壁生活艰苦的一家人身后,穿着那件红外套,戴着灰色帽子,架着近视眼镜,长发披到了背上,双手伸向天空。他们一起喊:茄子!
他的相机还对准了河上的垃圾,他不知道那些蛇皮袋、塑料泡沫、烂菜叶、小药瓶、高跟鞋和废油桶下面是一条河流。一点也看不出来,走着走着,河水才露了出来,上面漂着五色的油污。另一条河全然是铁锈红色,像红墨水一样,水面上没有一丝波纹。他拍下了红色水面上的古桥、石头房屋和孩子们。
集市边堆成小山的垃圾,城市郊区巨大的垃圾场,铁轨边细长的垃圾带,靠垃圾生存的村庄,站在垃圾堆上的老人和孩子……这些震撼人心的现代风景,他都拍下了。
他还拍下了杀戮。人们杀牛、杀鹿、杀猴子、杀虎、杀鳄鱼……地面被血染红了,人们用水冲掉。动物被肢解,头和四肢堆成金字塔,内脏挖出来丢在木桶里,皮被扒掉挂在墙上。阳光照耀着动物的眼睛。他拍下照片,男人们围上来,扯掉他的胶卷。放倒他。他起来,一只脚踢中了他的眼睛,他躺在地上。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人们问。
3
十年的行走分为五个阶段,线路盘根错结。第一阶段从哈尔滨102国道零公里处出发,穿越中原各省,到达香港澳门;第二阶段穿越云、贵、川;第三阶段是青藏高原,海拔越来越高;第四阶段走入新疆、甘肃、内蒙,去处越来越险;第五阶段,从东北再次出发,走沿海省份,最终抵达台湾。这一路设计的美丽圆满。
他的心路也分为几个阶段,从艰辛、孤苦、愤怒,到触摸死亡,然后越来越轻盈,越来越辽阔,越来越平静。
在阿里无人区,一种意外的灾难袭来,他从未防备:安静。不知是耳膜还是精神上的问题,他天天都听见有一个小人在耳朵里尖叫。晚上气温下降到零下20度,他一边睡,小人一边在他脑子里锯出一条流汁的细缝。他坐起来,在橘色帐篷里眺望远处的沙暴。白天走在50摄氏度的戈壁里,小人集体出现,在他前面齐声尖叫,像飞机引擎一样震动着他的鼓膜。
他焦躁不安。他想走出无人区,也许到那个广西小村庄和那家白族人待在一起,他知道她喜欢他。也许该到寺庙里和活佛学习跳脱轮回,他知道轮回是真有其事。也许先得回哈尔滨看看姐姐,姐姐早就打不通他的电话了。他喝下一口水,望着太阳,掉头走向另一个方向。
他醒过来时,才知道恐怖。他找回原来的方向。开始治疗自己,和自己说话,他用天津话和自己聊,“天津话管吃不叫吃,叫塞!管摸摸不叫摸摸,叫胡路胡路!管派出所不叫派出所,叫派所!管拳击不叫拳击,叫捣皮拳儿!管漂亮不叫漂亮,叫真遵。(四声)”
他30岁了,正是想大姑娘的时候。他不是该和姑娘看看电影,喝喝咖啡,从东城走到西城,再弄个家庭,再拉扯大一个小朋友?这样的生活不是自有迷人之处吗?吵吵架,做做饭又如何?一个静止的家庭和一条晃动的路,哪个才健全?
他回答那个说天津话的自己:“色即是空。”

从阿里无人区出来,他歇了歇,走了走平原,看了看鱼米之乡和小桥流水,然后又折返罗布泊。对着这个吞噬掉他的偶像余纯顺的地方,他心里有点异样。于是进入大漠之前,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如果去见了余纯顺,这封信就能代替遗嘱。他没什么财产可分,只有些债要还。
他进入罗布泊时,遇到了一伙黑龙江电视台的人。那些人打量着他,有心和他做一期节目,但是又怕出事。拍摄之前,要和他签个“生死契”。他们写了点东西,他在上面按了个手印。“太好了”他们说。
他在死亡沙漠里走了30天,来到了余纯顺的墓前。拜祭了偶像,睡在他的墓前,他觉得他就像父亲。生为行走的心隔空交汇,他忍住泪水,觉得内心融化,想问那个首次见面没敢问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走?
为什么呢?花为什么红?诗人为什么要写诗?歌手为什么歌唱?为什么有痛苦与欢乐?这都是伟大深刻的迷,这涉及人性和存在,涉及灵魂和意志,涉及世界的价值。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简单点呢?你的心弦到底拨弄着什么样的旋律?
是的,他小时候就听到了一首歌。那时他很孤独,父母在他14岁时相继去世。他在舅舅家寄住,总吃不饱,学会了不再嘤嘤抽泣。在干完一天的活之后,走进了长满了蒲公英的树林里,他和啄木鸟打招呼,与兔子缔结友好协议,他步入草从深处寻找一份神秘的节奏,那和他的心跳协调一致,能够使他平静下来。有时候他睡在母亲的坟上,过了整整一夜,露水滴在脖颈上把他弄醒,他感到很自由。他睁开双眼,鸟儿在头顶的树冠上啁啾。他铭记美丽的自然对他的爱和启示,它从未舍弃过他。
他那时就想走出去,走到更大的空间里,融入那个半神的世界中。他一直等着这一天,他舞着九节鞭,在工地上赚钱,在外企潜伏。每天跑10公里时,他脑子里没有别的,没有姑娘、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规范也没有计划,只有高山上的来风。他可以和整个世界跳舞,那里别无他人。
他在罗布泊看到了最最奇怪的东西,他不愿意多谈。
“你是说你看到了鬼魂?”记者问。
“我无法解释那是什么。”他说。
他在太阳升起时醒来了,继续行走。在烤焦的大地上,鞋子磨出了洞,他换上一双新鞋,背着旧鞋。他看到一些奥陶石、树化石,把它们装进背包,甩着长发走向沙漠中心。他的户外生存经验越来越丰富,这是一部长达10年的《荒野生存》,喝自己的尿,喝自己的血,吃蜥蜴、老鼠。为生存用尽一切智慧,穷尽人之所不能。
这么长的路途,不能不去拜会珠穆朗玛峰。他没有钱像王石那样搞,只能为自己增加90元的预算,在服装批发市场上挑了件红色棉服,穿着牛仔裤就开始爬山了。他一路向上,爬到了7000米。“哦,这里太高了。”他踩在冰雪上,环顾群山。几分钟后开始下撤。
2007年,他终于走累了。这是第九年。他的地图上所有的点已经快要闭合。他买了一个独轮车,把包袱、化石、猴子头骨和牦牛头骨、帐篷和被打劫的人打掉的牙齿都放在独轮车上,一路往回走。这样的车子可以行进在最狭窄的田梗上,还可以爬山,爬过了秦岭。他把它推到了天安门广场上。那是2008年,他看到这里到处是奥运会的旗帜。他从背包里拿出来一件东西,就着大风一送,从手里呼呼啦啦地飘展开。媒体追上他,他成了哈尔滨站的奥运火炬手。
“我哭了一次。走出罗布泊那天。我看到了公路,然后看到一座座灰色的旧房屋,我知道我好好地活着,经历了这么大的苦难,我还好好地活着。我走了31天,我想,我就想好好地活着。”他对着前面的世界哭嚎起来,他弯曲着自己的腰,鼻涕拉在半空,一个村庄正在地平线上升起。
现在,雷殿生是昌平作家村的1号居民。这里空气新鲜、山峦秀丽。作家村里时时会碰到莫言、阎连科和一些有回忆要写的政客。他在屋子里写作,一层的客厅里展示着他的宝贝,十年徒步旅行搜集到的纪念品和拍下的照片。一间书房里摆满了各地县志,他一路上把那些没人读的大厚本寄给未来的自己。帐篷和独轮小车放在角落里,烧掉一半撵跑了狼的外套,在帐篷上搭拉着。二楼是奖杯、奖状,一张印满邮戳的布和部分日记,字体狂野奔放:今天行程44里,比我预计少许多,等脚伤好转再补回来,走多少对于我来说都还是开始,路太长了……
现在的雷殿生,有一半活在记忆里吗?他接下来该怎么生活呢?
“哥们,你还能走吗?”光给GOTEX代言,给户外网站当领队,给富人和军队做培训吗?你能满足这样的生活吗?
生活真他妈的残酷,问题变成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