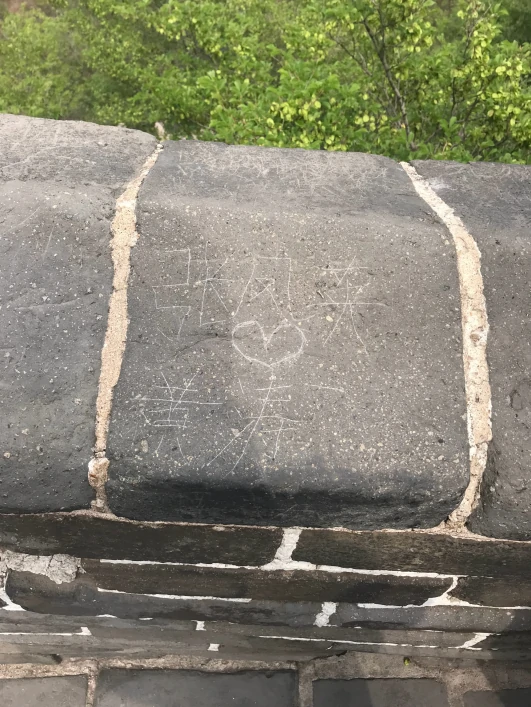不久前,我坐火车去西部出差,在郑州站换乘一列午夜时分到达的过路车。
在等车的几个小时里,结识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我称他为――“火车站广场之王”。
1
走下站台,进入地下通道,我没随人流走上出口处,而是由着脚步转向另一处通道。指示牌显示,这里通往出租车候车区。
候车区空旷清冷,中间撑了一排巨大的方形柱子,往里的那根柱子下面,躺着一个人,被一条破被单覆盖着身子,头脸露在外面。
走近,才认出来是位中年女人,正窝着脖子枕在一个深色的旧旅行包上,她头发凌乱,脸上骨骼突起,眼窝很深,像是在这里已经滞留了一段时间了。
经过她的卧身处,她低垂的眼皮突然翻起,用锐利的眼光盯着我,冷冷地说:“走开,离我远点!”
仿佛这是她的地盘。
我讪讪离开,由一处台阶走到地上,选择火车站的西广场作为暂留地。
天已经全黑,各家商铺招牌上的霓虹灯闪烁着光彩;火车站大厅入口上方巨大的电子屏幕正在播放广告,一帧帧画面迅速切换,将浓重的色彩映在旅人的脸上,忽闪忽闪地不断变幻。

顺着广场上的一排不透钢栏杆,隔两步远就有个生意人在叫卖,“充电宝便宜了,35块钱一个。”“矿泉水,矿泉水,一块钱一瓶。”
她们多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面前铺了块方布,上面摆放着充电宝、手机壳之类的小商品,用小夜灯映照着。旅客匆匆而过,没有人在摊位前停留,生意很清淡。
我背抵着栏杆站了会儿,觉得累,就把身子溜下去,半个臀部搭坐在水泥基座上。
“啪”,一个折叠马扎甩在我身前,“在那儿坐着不凉吗?来,坐下。”
那是蜷缩在栏杆旁的那个人,他也摆着地摊儿,但摊位比别人明显要靠后些,摊位前面还放着一个破纸桶,底部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身上则裹着一件褪了色、走了形的军大衣,半躺半坐地倚着栏杆,一双扭曲的腿露在外面。
他境遇不佳,开口却是掌控者和施予者的话语。
2
我顺从地起身,移到马扎上,与他拉近了些。一股陈年的腐臭味儿夹杂着浓烈的酒气刺进了我的鼻孔。
“谢谢。这样舒服多啦。晚上喝了点?”
“半斤多二锅头,56度的。”
他用胳膊肘支撑起上半身,动作从容缓慢,语速不慌不忙,“我看你戴着眼镜,像模像样,才让你坐。你以为谁都能坐?昨天有个女人,站在那里对我说:‘喂,要饭的,坐坐你的马扎。’我当时就把她给撅回去了:‘哪个姓魏?对不起美女,我这马扎是要卖钱的。’――求我事儿,连句客气话都不说,把我当什么?”
我做出感激的表情,再次道谢。
“你是哪里人?”
“山东聊城。”
“聊城?离我老家很近,我是濮阳人。”
“我十多年前去过,那时濮阳就很漂亮,街上的绿化很好。”我拣着好话说。
“美不美管我鸟事。你等火车?打算去哪儿?”
“甘肃。”
“甘肃那么远,你需要一个充电宝。小心路上手机没电了,耽误大事。”
“多少钱一个?”
“65。”
“太贵了。人家都卖35。”
“他们能和我比?”他醉眼迷离,挥手隔空划拉了一下前面的几个叫卖者,“现在城管下班了,等城管一上班,他们全都得给我撤,到那时我才算正式开业。只我一家,想卖多少就是多少――昨天卖了俩,一个一百。”
“你不怕城管?”
“怕什么?他们毫毛都不敢碰我一根。”他的眼睛移到自个儿的腿上,示意给我。
“你的腿脚……可以走路吗?”我小心地问。
“我一口气可以跑两公里,但是城管来了,我一步都不会走。”他用力摆了摆头,抽出两支香烟,递给我一支。
“你在这儿多久了?”
“有几年了……说不清。过一天是一天,我不操这份心。”提及往事,他开始忆苦思甜,“那时他们不认识我,还没收我的东西。我到他们办公室门口一躺――你们不让我活了吗?大队长还不是得乖乖把东西还我。”
他讲得兴奋,突然直起脖子叫了句:“城管来啦!”
摊主们慌忙转身四望,近处的一位老太太回身骂他:“傻要饭的,发什么疯,吓死人你偿命!”
他开心地笑起来。电子屏幕上正播放一则食物广告,浓重的色彩打在他灰暗的脸上,照见一层油泥和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身后的广场上有人在甩鞭,尖利的声响穿透了嘈杂的人声。
我抽出两支烟,让过去一支,帮他点上。
3
他果然不是个平常要饭的。
他说他生在城里,父母都“吃皇粮”,父亲曾是某个厂的会计,现在已经退休;弟弟和弟媳都在机关里做公务员。
“过年回家的时候,兄弟媳妇叫我哥,我都不好意思应。”说起自己的身世,他高亢的声音低沉下来,迷离的眼神落在面前来来往往的腿上。
他从小就有小儿麻痹症,读书时受了不少欺负,但还是坚持读完了一所职业高中,毕业后成为郑州一家食品加工厂的正式职工。可做了没几年,赶上了厂子改制,他被辞退后只能按月领一点生活费。
他也拖着腿一歪一斜地到处找过工作,可没有人肯用他,只得回到老家。
“很没面子,”他说,“人都要讲个衣锦还乡。我本打算在郑州成家立业、闯出个名堂的。”
家人帮他四处托人,给他娶了亲,对方也是位残障人士,智力低下,什么活也做不来。没几年,两人就离了婚――“那婆娘不能给我生孩子,要她干什么?”
此后,他以酒为伴,揣个酒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醉了,躺倒在街边就睡着。他说,“不喝酒时你在那儿站着、坐着,喝完酒就腾云驾雾上了天,自己变成了老天爷爷,什么都敢做,什么事都难不住你。”
那点生活费经不住折腾,他只好向父母伸手。爸爸点钱点得仔细,就算只给几张钞票,也要慢慢点上两遍,叫他等得不耐烦。这样时间久了,次数多了,终究是不愉快。他也不想再拖累家人,再次只身来到了郑州,在火车站广场做起了乞丐。
见人家摆摊能赚钱,他也学着做起来,算是个兼职。他告诉家人已经在外面找到了工作,整年不回家,只在春节时团聚一次。
“过年的时候,我就换身干净衣服,人模狗样地回家。谁管你在外面做什么?”
4
除了旅客,他好像认识广场上的每个人,保安、店员、附近宾馆的掮客……他边和我聊天,边不时嘻笑着和老熟人打招呼,说上两句浑话。
他与社会毫不脱节,只要是女人,不计较年纪和相貌,他一律称为“美女”。有位手拿着“住宿”牌子的半老女人走过来,他又挺直脖子兴奋地叫:“嗨,美女!我要住宿。”女人没好气地说:“住你个鬼,老实睡你的石头板吧!”
近处的那位老太太做成了一单生意,顾客付了一张百元钞票,她拿过来让我的乞丐朋友鉴定真伪,“要饭的,你给我看看,真钱假钱?”
“美女发财啦,”他接过钱,也不看,只用手一摸,“真的,放心收着吧。”
“你看都不看,就那么确定。”
“那还用看。你就用手摸毛泽东的头――头发丝儿一根根嗤嗤地挂手指头,就假不了;摸他的衣领儿也行,那儿也‘起沙’,谁也骗不了我。上回有个女人买马扎,拿张20块的假钱,我扔还给她,‘你骗鬼呐!这是你家印的钱?使用假币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夜深了,广场上的人来来往往,神色匆忙,站楼里的扩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火车班次信息,催促着旅人赶快上路。
“你是几点的火车?买一个充电宝吧,给你算便宜点。”他又想起了正经事。
“12点半。”我告诉他自己带了充电宝,又问他:“你们卖得那么便宜,网上都没有这个价,进货要多少钱?”
“商业机密。”他狡黠一笑,停了一会儿,他忍不住了,对我说:“15块,全是假货。看你厚道,不瞒你。”他指了指那个给小夜灯供电的充电宝说:“只有我自己用的这个是真的。”
“没人回来找你退货?”
“卖给他们之前,我先问他们坐几点的火车――假充电宝只能充3个小时的电,只要3小时之内发车,我就放心卖喽,他总不能从火车上跳下来找我吧?”
“哈哈,人才。”我忍不住笑起来,“每天进账有多少?带上那个纸桶里的钱。”

“这也是商业机密。”他神秘地笑笑,反问我:“你呢?”
我告诉他自己的工作收入情况。
“你上班也是过一天,我要饭也是过一天,我无牵无挂比你舒服。”他又慢腾腾地从怀里掏摸出一支烟,“我一天8小瓶二锅头,40块;3盒黄金叶,33块,你算算,赚得少了我能活下去?
“消费水平挺高啊。吃饭还得花钱吧?”
“我是干什么的!我专吃德克士、肯德基、永和豆浆!老板们去那里吃饭,一买就是三、五个鸡腿,一笼蒸包,吃剩了,服务员就给我送来。”
“睡觉呢?你不会真的去‘住宿’吧?”
“这个百宝箱就是我的枕头,”他拍一拍身旁的破皮箱,“上天就是我的被子。”
“会不会丢东西?你这么多宝贝。”
“东西没丢过。有时我醉了,睡着了,会有人把我纸桶里的钱拿走。”说到这儿,他突然醒悟似的看着我,“你不往里面投点钱,意思意思?”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币,面额稍大,但不好意思塞回去,起身放到了纸桶里。
“哈,哥你别吓我。”他睁大了细眼睛,“等会儿你带着那个马扎上火车,算是你买了它。”
5
午夜时分,人声渐渐沉寂,站楼后面传来火车低沉却很有穿透力的呜鸣,广播里温柔的职业化的女声仍在一遍遍提醒旅客进站。我伸手去摸烟,烟盒已经空了,转而掏出手机,摁亮了屏幕。
“你的火车要来了吧?”他仍保持着那个蜷缩着双腿、用手臂支撑着上半身的姿势,脸上毫无倦意。
“嗯。很快了。”我站起身和他道别。
“进站口在北面。”他抬手指给我。
“我先去对面买盒烟。”
“火车站你买不到真烟,告诉他,就说是对面那个要饭的介绍你去买的,他才会给你拿真烟。”他说这话时气定神闲、不容置疑。
我相信他的话,向他道谢,但走到那个窗口却没有按照他教我的话说。
“喂!”他在对面大叫,挥舞着手臂,“给他拿真的……也给我送盒过来!”
“操,臭要饭的。你自己来拿!”店主大声回应他。
10天后,我从甘肃返程,仍在郑州站换乘火车。到达车站时是凌晨6点多钟,广场上的雾霾压得很低,稀稀落落的旅客面目模糊、动作迟钝,游魂般迎面飘过;风吹着几个塑料袋在地上走走停停,飘起来又慢慢落下去。
我的乞丐朋友正蜷缩在栏杆下面的昏暗里,一动不动,睡得很香。他的身子转了个方向,不再面朝人行过道,而是顺着栏杆躺卧着,想是怕被过往的人踩到。
我又冷又饿,去面馆吃了一碗茄汁面,吃完就径直走进了候车大厅,没再去打扰他。
今天下雪了,温度降到零度以下,街上的人躬背缩肩,小心翼翼地踏着冰雪行进。冬天按着它自己的轨道隆隆驶来,不知那个睡在火车站广场的人可好?但我知道:就算他在颤抖,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