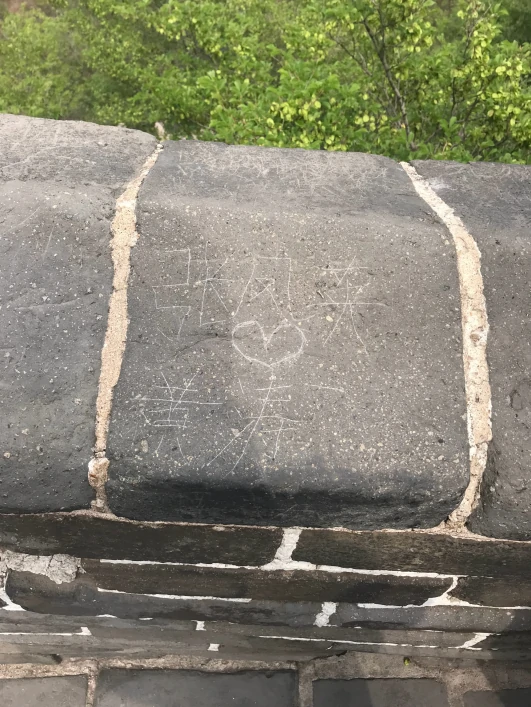90岁的母亲大病初愈,住进了县城的老年公寓,虽然生活能够自理,但大脑却时而清醒,时而混沌。每次我去老年公寓看望母亲,老人家就反复向我絮叨着一件事:在土匪家当童养媳。
此前几十年间,我却极少听母亲提起这段伤心往事。
1
1927年,母亲出生在豫东平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姥爷和姥姥养育了三男三女,母亲排行老三,生下来就几乎没过一天好日子。
母亲回忆说,1938年日本人来了,眼看就要过黄河南打到开封,蒋介石下令国军扒开了黄河花园口。一时间,黄河水顺流南下,老天爷又帮倒忙,连续下了几天倾盆大雨,田野里汪洋一片,我们一个县,就淹死了两万多人。
那年头,土匪蟊贼遍地,为了生存,打家劫舍,绑票勒索,闹得民不聊生。姥爷和姥姥为了活命,匆忙将我大姨嫁出去,接着把我当时11岁的母亲送进土匪窝当童养媳,他们带领三个舅舅和小姨闯关中,落脚在陕北黄土高原。
母亲摇头叹息,“在老一辈人的心里,只有儿子才能够为家庭延续香火,爹娘狠心撇下俺,临走就留下一条薄被,三九天冻得我浑身直发抖,扒拉一堆麦秸盖身上。”
母亲当童养媳的村子,正好是我曾祖母的娘家。那个名叫孟楼的偏远小村落,二十几户人家挤在一条黄土高岗上,没有被黄河水冲淹。全村清一色的孟姓,家谱记载都是孟子后裔,实际上却因匪名远扬被载入地方志。
曾祖母的娘家有5个莽壮侄儿,个个舞枪弄棒,号称孟家五虎。最初,我的大表爷带着弟兄几个白天种地,夜晚奔波几十里路程,专拣外乡的地主老财抢劫,从来不吃窝边草。
后来,大表爷兄弟几个成了气候,全村男丁都跟随他们掂枪为匪,连附近的杆子也投奔而来。大表爷自封“游击司令”,腰插双枪,身背大刀,带领众弟兄远征太康县老河口,打得日本人一个月过不了河。新四军豫皖苏军区28团团长亲自登门拜访,跟大表爷大碗喝酒,招抚他归顺共产党。只可惜,那天夜晚,团长在归途中遭国军截杀身亡,未能如愿。
母亲的男人是我大表爷的族侄,家中有二亩沙岗薄地,弟兄俩整天游手好闲。母亲进门没几天,婆婆因病去世,那个男人在赶集路上又被国军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家里只剩下大伯哥和母亲两人。
偏偏,家乡遭黄水冲淹过后,又赶上大旱和蝗灾,三伏天不下雨,庄稼叶子被蝗虫蚕食,饿殍遍野。
在母亲的记忆中,祸不单行,婆家大伯哥擦枪走火,子弹从前胸穿透后背,打烂了肺叶。因无钱医治,大伯哥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家庭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肩头。
麦天里,十几岁的母亲独自下地收庄稼,割完麦子,雇佣大表爷家的太平车往家里搬运。交换条件是,整个麦天,母亲都要帮大表爷家义务干农活,单薄的身子骨硬撑着,身边孤零零,一个怜恤的亲人都没有。
冬去春来,大灾年苦熬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在家揭不开锅了,伤口化脓的大伯哥仍躺在床上半死不活。
那时候,我的老家地势低洼,房屋土地全部泡在了黄水里,爷爷奶奶带着单根独苗的父亲投奔到舅舅家避难。为了生存,奶奶每天推磨磨面,与村人合伙支起一口油锅,靠炸麻花糊口。
母亲就去找我爷爷求情,到麻花摊上赊账卖货,每天挎着竹篮早出晚归,一天下来,碰上生意好时,能赚三根麻花。母亲自个舍不得吃,将麻花拿回家 ,搁锅里配上野菜和树叶煮成稀汤,用勺子舀着一口一口地喂大伯哥。
就这样,母亲在灾荒年不但没饿死,还将大伯哥给救活了。
20多年后,大伯哥从新疆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路过我家吃午饭,提起当年的旧事,千恩万谢,一个劲儿叙说母亲的好处。
2
大伯哥被人民政府判了刑。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的家乡一带属于游击区,新四军独立团越过新黄河,到水西开辟根据地。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土匪武装也经常驻扎在这里,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在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共产党武装了解到我母亲出身贫苦,想让她出头当妇救会主任,母亲身处土匪窝,整天提心吊胆在刀尖上过日子,就婉辞拒绝了。
村里跟母亲同病相怜的另一个女人,男人被抓壮丁的打死了,独立支撑着门户,天不怕地不怕,就应下了妇救会主任的差事,却招来一场杀身之祸。
母亲如今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心有余悸,老人家声音颤抖着说:“那是一个有月亮光的夜晚,俺看见孟家老四召集几个年轻人,提着手枪叫开那女人的家门,不由分说就掐住了脖子。冷不防被那女人反咬一口,咬住孟家老四的手指头,疼得他嗷嗷叫。恼怒的老四顺势把一支枪管捣进女人嘴里,活泼啦啦的女人瞬间就咽了气。”
那天晚上,母亲躲在墙豁处,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几个年轻人抬着那女人刚断气的热身子,一头纷乱的长发耷拉在地上,不声不响弄到东岗给埋了。
事隔不久,随着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古城,豫东平原宣告解放,我的大表爷和四表爷被人民政府就地处决。大伯哥也因当土匪劣迹斑斑,被判处无期徒刑。
母亲终于结束了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经人撮合,与未婚的父亲组建起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母亲过门就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精打细算过日子。”
“母亲过门就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精打细算过日子。”
母亲进入父亲家,依旧吃了不少苦。
我大爷膝下无子,跟我爷爷老弟兄俩守着我父亲一棵独苗,使得父亲自幼娇惯成性。身为农民,却一辈子不会扬场放磙、摇耧撒种。母亲过门就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精打细算过日子。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呱呱坠地的头一天,就赶上村里吃大锅饭。母亲把我放在村办托儿所里,拖着虚弱的身子下地割麦子。
托儿所里,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太太,看护十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任其忍饥挨饿,甚至哭哑了嗓子,也顾不上管。母亲怕我饿死,央求队长开恩,把我带到田间地头,好半晌给我喂一次奶。
母亲最难忘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父亲应招到豫西矿山当工人。父亲前脚刚走,六月天,大奶奶就病逝了,当时不通电话,路途又远,联系不上父亲归乡奔丧。
按照豫东乡下的老规矩,家族里有男丁的,女人是不能为死去的长辈摔老盆送终的。无奈中,母亲披麻戴孝,一只手抱着大奶奶的灵牌,另一只手掂着老盆,替父亲尽人子之孝。
回忆当年的情景,母亲眼眶湿润,“送葬路上,俺哭着喊一声‘娘啊’,当街摔碎了老盆,那场面让围观的街坊邻居纷纷落泪。”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虽然不富裕,却在村里率先购买了缝纫机,盖起令人羡慕的青砖大瓦房,父亲也如愿以偿骑上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
母亲自学裁剪,不仅将我们6姊妹穿戴打扮得干干净净,还为村里几百口人裁剪做衣服,成为乡下远近闻名的裁缝。
若遇上村里突然死了人,来不及准备寿衣,母亲将缝纫机抬出来,从头到脚为死者做衣服,紧张忙活一天,把两条腿累肿了,却不收分文报酬。
3
上世纪70年代,随着我们6姊妹长大成人,三姐参加了工作,我也当兵在部队面临着提干,母亲觉得苦尽甘来。
可那笑声未尽,因我赴南疆参加战争生死未卜,母亲就又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1979年2月,我随部队出征广西边境,身负重伤被抬下战场,转诊于野战医院急救室,切开气管靠呼吸机输氧维持生命。
那段时间,母亲天天听广播,神经是最敏感的。宣布撤军之后,村里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都寄回了平安家信,我却杳无音信,母亲直觉出了问题,急忙让父亲卖掉家中仅有的一些红薯干,凑足路费搭火车往南寻找。
从豫东到广西,三千里路途,为了节省钱,父母饿了,舍不得吃火车上的盒饭,就啃几口随身携带的干馍。沿途不断有军列载着伤员往内地转运,母亲瞅着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孩子,始终看不到我的身影,哭得两眼红肿。
在湖南衡阳车站,母亲因悲伤过度,又喝了厕所里的凉水,腹泻虚脱躺倒在站台上起不来。父亲担心母亲的身体,苦着脸说:“不行咱回去吧。”
母亲闻言急了,两眼流泪,“咱就这一个儿子,活要见人,死也要找着埋在哪儿。”
车站乘务员问明情况,让母亲服用了止泻药,还端来了热饭。母亲的精神头稍微好一点,便强撑着站起来,在父亲的搀扶下,继续向南边寻找。
一路上,父母见到穿军装的人就问,靠着挨个到野战医院打听消息,最终在南宁市303医院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
那天上午,抢救室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了,躺在病床上的我见父亲扶着母亲跨进门,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
母亲见我骨瘦如柴,俯身用粗糙的手抚摸一下我的额头,轻声抱怨说:“出恁大的事儿,光瞒都中啦?”
母子四目相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母亲反倒安慰我说:“孩子,咱不哭,活着比啥都强。”
母亲的出现,让我孤寂的精神得到慰藉,以顽强的意志力分分秒秒与死神抗争,终于赢得了属于我生命的5%生存空间。

此后,我由广西转入豫北野战医院疗养,因全身瘫痪,医生诊断说,我要躺在床上一辈子了。
母亲不甘心,在乡下四处寻医问药,找到一个祖传老中医,让父亲把老中医请进医院为我诊治,每月坚持服用中药丸。
那中药丸40元钱一个疗程,能吃两个月。在我住院疗养的两年间,父亲按时从豫东到豫北医院给我送药,从没有间断过。而当时的40元钱,是一个农村家庭半年的生活开销了。
母亲卖掉家中饲养的猪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自己珍藏多年的3块银元也从箱底翻出来,卖了15元钱。最后实在弄不来钱,母亲舍下脸皮,四处求亲告友,借钱给我买药。我终于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至今想来,假如当年我牺牲了,成为南疆烈士陵园的一方墓碑,哭倒在墓地的一定是我的爹娘。视儿如命的母亲,面对丧子之痛的打击,也很难活到如今的高寿。
尽管我的四肢重度残疾,但因我的存在,这个家才完整,父母就能看到生活的希望。
近几年,随着我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各自成家让我抱上孙子,高寿的母亲也熬到了太奶奶的尊位。
去年春节,我的小儿子开车将两位老人接到郑州过年,目睹一家人四世同堂,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母亲享受着弄孙之趣,心情释然开怀。
母亲怀抱着曾孙子乐呵呵地说:“咱家后继有人,俺还能再多活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