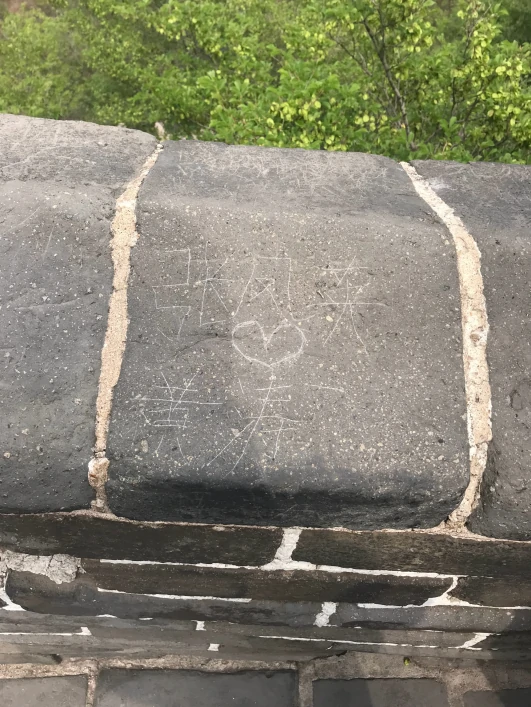自述在我隘口村的亲人中,外公外婆与我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几乎都还停留在传统方式阶段,社会激烈的转型也并未直接渗透进他们的日常。2007年1月,我外婆去世时,已经93岁高龄。我的舅舅辈,在90年代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热潮中,因为年龄和家庭结构,都没有外出打工,但子女大多在这一阶段成人,他们通过子女,不可避免地和社会产生了关联:满舅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害者,儿子鲁智吸毒、买码、赌博,让满舅的人生也随着陷入泥坑;二舅是这一转型的受益者,在二舅的人生设想中,最美满的结局也无非是招一个可靠的上门女婿,名正言顺地依赖女儿,养老度日。二舅从来都没有想到,女儿鸿霞最终会在深圳这片热土中获得成功。舅舅这一辈的人群,恰恰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过渡性最为明显、感受最为深切的一群。一方面,他们见证了国家的多次嬗变,有着天然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他们勾连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有着更为丰富、完整的经验。以我的二舅为例,他出生于1947年,经过了“四清”、“五风”、“大集体”、“文革”、“改革开放”等阶段,对土地有着深入骨髓的情感,但因为要帮独生女儿鸿霞照顾孩子,从2005年开始,他不得不离开土地,和舅妈一起来到深圳,一待就是十几年。二舅的深圳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完整的城市生活经验。而二舅眼中的村庄变迁,不仅折射了他个人命运的流转,更凸显了他对隘口村命运的整体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出的是一个中国农民对农村命运的真切关注和反思。
1
在我家,我们叫二舅为“爹爹”,叫舅妈为“妈妈”。爹爹和妈妈,本是隘口村孩子对父母的称呼,因二舅和舅妈自1967年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我们这些侄子、外甥便依据风俗,全部称呼他俩为“爹爹、妈妈”,几十年来,从未改口。
1976年,二舅生下女儿鸿霞,那时我已到外婆家居住,整个童年阶段,我和鸿霞一起长大,形同姐妹。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总得有人负责调停家族内部事务、动员家庭成员共同面对家族困境。二舅的存在,便是如此。二舅为人耿直、脾气大,但对孩子极为和气,我童年与父辈相处的温馨记忆,几乎全部来自二舅。他带我们做游戏,拉成一圈,村里十几个孩子叽叽喳喳跟着他,带我们唱儿歌,“麻雀子灰里面滚一滚,哥哥怪我�买粉,买得粉不晓得发,哥哥怪我�买鸭,买得鸭不晓得箝,哥哥怪我�买盐,买得盐不晓得放,哥哥怪我�买酱……”
年关未到,二舅便早早得和外公准备年货,给孩子们做灯笼、买大炮,二舅甚至容忍我们给他化妆、扎小辫、画花脸、用胭脂花涂指甲。面对孩子们的恶作剧,他从来不会一本正经,也不会轻易动怒。
等到七岁半,其他表弟表妹都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因为太忙,顾不上我,二舅便主动将我送到学校,结束了我整天和外公放鸭子的童年时光,开始了蒙昧的读书生涯。到小学三年级,他开始教我写日记,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至今。
二舅待每个孩子都如此,但所有的孩子中,只有我最听他的调拨,他因此有一份特别的满足和成就感。整个高中阶段,除父母以外,二舅是唯一特意到学校去看我的亲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当时给了我十块零花钱(1990年)。
现在看来,在养育孩子方面,二舅确实有很多来自生活中的智慧,他始终认为野性是孩子的天性,不野性的孩子,长大了蔫不拉几没有用;对于当下家长完全按照书本带孩子,整天神经兮兮、过于紧张的心态,他认为完全没必要。以家长极为担心的“小孩子吃零食”为例,他的解释是,小孩就像小鸡一样,东西吃得再多,也容易消化,适度满足小孩贪吃的天性,并不过分。
二舅一辈子秉承着勤俭持家、动脑经营的理念。“人要勤快,要动脑子,起家才快,我一年365天没有一天空,落雨天就待在家里做事。”他信奉最传统的价值观,有明确的道德底线,“害人的事我坚决不搞,别人害我也不怕。人做歹事天知道,迟早会遭报应。”
二舅热爱读书,尊重知识和技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七八十年代,他经常收听广播,喜欢鼓捣一些奇奇怪怪的技术。房前屋后,不是摆满了养殖的蘑菇和菌类,就是培育的飞蛾和蜜蜂。除此以外,二舅还一直坚持酿酒,从别处买来粮食,自己酿造白酒。冬天的凌晨,发酵谷物的香味,伴随轻柔缓和的搅拌声,多年来一直沉淀为我童年清晨最芳香的记忆。
对于1947年出生的二舅而言,将近七十年来,他从未离开过村庄到别的地方定居,也从来没有想到去镇上或者县城买房、和时下的潮流一样进城定居。在二舅身上,我从没有看到农民身份带来的宿命般的悲苦,也没有看到一丝底层农民的哀怨和自怜。他热爱自己出生的村庄,对土地有着亲人般的情感,一直到今天,他都坚持农村的日子比城市好。
2
尽管隘口村的经济条件,相比周围的村庄和乡镇,要略好一些,但在过去的年代,二舅和他同龄人一样,也吃过很多苦。
在他看来,最艰难的日子,依然是1958年“大集体”时饥饿的记忆。二舅始终记得,11岁的他带着9岁的妹妹,整天到外面去挖黄花菜。外婆为了让黄花菜好吃一点,每次都竭尽全力挤掉苦水,但再巧的手,因为缺盐少油,做出来的粑粑依然难以下咽。二舅提起有一次,在工房推磨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了一个稻草粑粑,却被队上的“国癞子”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1967年,二舅和舅妈结婚,日子依旧艰难,外婆、外公给他们分了两间房,没有配套的茅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二舅一直想多做一间房,以改善居住条件,但因为搞村庄化,没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好不容易准备了一点泥砖,却没有稻草;好不容易准备了一点稻草,却缺少木材;搭建房子的心愿始终没有实现。
尽管这样,二舅还是会见缝插针地想法子改善生活,不能明目张胆地干,就偷偷地干,集体时代分得的有限稻草,二舅会想办法增加其附加值,一到晚上,就躲在家里偷偷将稻草打成绳子,一个晚上可以打四根,然后悄悄卖给供销社。其他家境困难的农户,也会将稻草卖给二舅,二舅经过加工后,赚取其中的差价。
“不要小看打绳子的手艺,它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你大姐那时送到鲁家�,一两岁的时候,总是坐在家门口等饼吃,她知道我每天卖掉绳子,就会从街上带饼回来。你妈妈嫁到三江后,做缝纫没有机子,也是我通过打绳子出本钱,偷偷给你妈妈买的缝纫机。如果不做一点副业,日子根本过不下去,现在看来,打绳子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解决了亲人的很多问题。”
对二舅、舅妈而言,最难接受的事情,则是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舅妈来自峒里的一户贫苦农家,为了挣更多的工分,做姑娘的时候,一直被当作重要的劳力使用。她小小的个子,竟可以挑一百多斤,一走就是十几里。“长大了就靠工分吃饭。十五六岁就要担担子,担一担谷子,要跑十几里。谷子太重,田坎上不去,人可以倒,但谷子不能撒,人倒了就爬起来,咬紧牙关担下去。那时,鞋子没有好鞋子,袜子没有好袜子。要外出,还需要借衣服。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谈念书,在娘家,必须做重功夫。”
舅妈的经历和我湖北的大姐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庭困难,到了婚嫁的年龄,依然只能待在娘家挣工分,以减轻经济压力。舅妈出生的地方在山边,阴冷、湿气重,做姑娘时经常下田,常常浸泡在冰冷的水田中,加上超负荷的重担,导致她的身体非常虚弱、以致婚后始终难以怀孕。这对喜爱孩子的二舅而言,是最大的折磨。
经过将近九年的调养,直到1976年,舅妈才生下唯一的女儿鸿霞。此后,多要几个孩子的愿望,就成为二舅、舅妈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童年印象中,舅妈最投入的事情,就是敬神求子,以致总有算命的跑过来,预测舅妈哪年哪年会怀孕。舅妈欢欣鼓舞,为此付出了很多财物,多一个孩子的愿望,却始终未能实现。
3
客观的讲,因为外公一直在生产队看鸭子,相比别人家中的日子还算好过。
当时的规矩是,鸭子生一斤蛋,可以获得一斤粮食的指标,外公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指标,细心照顾鸭子,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收获两三斤鸭蛋,换取到同样数量的粮食,意味着一家人的生存,能够获得最低保障。
“大集体”解散后,外公还一直保留着放鸭子的习惯,我童年的日常游乐,很大一部分记忆,就来自跟着外公,去村里的池塘、沟渠放鸭子,拎着小小的食筒捡拾鸭蛋。
只可惜,在物质整体贫瘠的时代,就算尽力经营,因为子女太多,有限的收入,还是难以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二舅结婚以后,曾经尝试改善家里的生活,但始终没有太大的空间,舅妈到今天还在唠叨,“文革”期间,因为偷偷在水塘里种了几颗高笋、就被告知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还被要求一定要种水秀花。
二舅的日子真正好起来,始于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松动。他原本就是点子多的人,加上勤劳,极大地释放了他的能量。隘口村人多田地少,分田到户并没有给二舅带来实际的好处,几分田的谷物,仅仅只够一家三口的口粮。但对二舅而言,改革开放最大的实惠,是让他获得了光明正大做生意的机会。
1983年,当年长乐镇供销社一个叫罗胜的职工告诉二舅,“现在政策放开了,你只要办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开店。”二舅找到税务所,卖掉一头猪做本钱,毫不犹豫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办好税务手续后,我获知可以经营南杂百货,买了几个亮瓶,买了几个架子,开着手扶拖拉机,从街上进了一些货,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二舅将店子开在东边的一间房子里,取名“益群商店”,“益群”是二舅的名字,“益群商店”是隘口村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独立经营的个体户商店。
商店开起来后,在村里小孩眼中,就成了全世界上最神秘、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为了降低成本,二舅自己生产很多食品,他不喜欢批发部买来的红姜,嫌它色素太多、味道太甜,他知道隘口村人的口味,经常买生姜制作盐姜;他不喜欢批发部的果脯,嫌糖精太多,过于甜腻,村庄的李子刚刚挂果,他会上门说好,收购一些,制成咸李子;二舅的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简单,他始终坚持卖给别人的零食,也能给自己的独生女儿吃,能给自己的侄子、外甥吃。
因为有商店做依托,二舅酿酒的手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担谷赚一担谷”,酿酒的利润高,但付出的劳动多,确实让人非常劳累。除了酿酒,二舅同时还学了做酱油、果汁和汽水,相当于生产、销售一条龙。
在80年代初期,乡村商店丝毫没有沾染今天唯利是图的气息,更多时候,类似于村人的一个聚居之处,对很多村民而言,手头紧张时,因为是熟人,会直接到店子赊账。二舅白天干活,舅妈负责守店,但舅妈不识字,我念小学后,总是要趴在柜台上,替她分担记账的任务。
舅妈记忆力特别好,五桃买了两毛钱的酱油,三红买了一斤柿饼,贵癞子拿了一包烟,她从来不会记错。有一个仲爹,对孙女极其宠爱,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让孙女骑在脖子上,老远就开始喊门,“老益,老益,买东西”,好几年,每天的开张生意都被仲爹包揽。
现在想起来,二舅生产的食品,真是物美价廉,让人放心。二舅生产的理念就一句话,“做吃的,要凭良心,不能害细伢子,你们也要吃的。”他生产的酒,自己喝,兄弟也买,他生产的零食,是女儿霞姑娘的必备。
熟人社会的信任,让这一经营充满了温情,也极大改善了二舅的经济状况。
4
二舅并没有沉湎于做生意带来的利润,对于教育,他有着更为强烈的痴迷。
“我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吃苦坚持念书。我读到了初中,你外婆胃气疼,要我回来煎药,后来就没有去念书了。你大舅成绩好,念到了湘阴一中,但你外公怕他调到外面去,将他叫回来了。只有你满舅,真的不喜欢读书,不是读书的料,一年级上了几个,名字里面的那个‘东’字,钩子总是写反。”
二舅没有完成的心愿,化作了对所有孩子的期待,我们几个同龄表兄妹的启蒙教育,完全来自二舅的管教,对独生女鸿霞,他更是不计成本地投入。
80年代鸿霞还在念小学时,他就知道送她学唱歌、学跳舞,刚进初中,为了支持女儿学音乐,他去县城买了一台风琴,拖到镇上,为了省下四块钱的板车运费,他心一横、将琴扛了回来,以致汨罗教育局的人,到现在还在说,“长乐街一个农民,舍得花几百块钱买琴,却舍不得四块钱的运输费。”
上高中后,二舅又很有远见地让女儿学外语,每个周末带她去湖南师大补课,一个月的开销就要一千多元。这些投入相比当时的收入,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支付能力。在整个农村都并不重视子女教育的整体氛围中,二舅的存在,确实是一个异类。
事实也证明,他的远见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回报。直到后来,我也才逐渐发现,一个家庭的长久兴旺,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条件的富足,良好的教育才具有更持续和长久的意义。尤其是在80年代往后的隘口村,很多一夜暴富的人瞬间丧失财富,将自己的人生弄得无从收场。
也许,在二舅的潜意识中,对教育的执着来自满舅的教训。
尽管亲人将满舅的败落,更多归结为运气不好,但二舅对此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你满舅的失败,归根结底来自没有文化。”
满舅聪明,但因为没有读书,吃了很多暗亏。例如有一次,给浙江的厂子打电报,将“钱没收到”,写成“全猫收到”,以致厂长打电话来询问,告知从来没有寄过猫;搞丝绸厂,从长沙买丝来做,越做越亏,二舅给他算账,才发现他的支出部分,只包括了丝的成本,员工的工资、工厂的电费,都没有计算在内。
满舅的果决和眼光,曾让他在80年代初期的草莽时代,获得过短暂的辉煌,但没有文化的短板,终究让他在一次偶然的骗局中彻底败落,难以翻身。
二舅意识到这一点,竭尽全力帮助满舅教育孩子,儿子鲁智在满舅身边读到三年级,二舅发现他连“九诀表”才能背到2。为了不荒废他的学业,二舅强行将鲁智带在身边,每天晚上辅导他的学习。“我说一句,他就写一句,我不说,他就咬着铅笔。我只好规定他每天必须写日记,写得出要写,写不出就抄写别人的句子。”
2016年春节,鲁智为了表达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将他南下的生活全部告诉我,同时给我看了他很多当时的书信。阅读鲁智的书信,我发现他很喜欢抒情,尤其喜欢抒发对亲人的抽象感情,哪怕在监狱的环境,一种小学作文的抒情笔调,总是流露笔端;他还喜欢景物描写,喜欢心理描写,这些专项训练过后的痕迹,想来都是二舅当年对他的用心。
二舅还责怪满舅太爱热闹,家里总是车水马龙,吃喝玩乐,通宵打牌,整天处于一种闹哄哄的状态,孩子根本就没有心思学习。他将鲁智带在身边,一直到他上初中。可惜鲁智生性顽劣,尽管坚持读完了初中,迫于家庭的压力还上过卫校,但终究还是走向了邪路。二舅对此也深深遗憾,“读书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是为了明事理。有技术能力,可以发展生产。睁眼瞎,只能懵懂一辈子。”
5
满舅的能力和影响力原本在二舅之上,但满舅运气不好、家道败落,更何况儿子不争气、吸毒坐牢,自己的生活都总是陷入焦头烂额,不要说去调解别人的矛盾,自家的很多麻烦,都还要依赖二舅出面化解。
鲁智吸毒坐牢,岳父岳母数次逼迫其离婚,最危急的一次,妻子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女方家庭却坚持离婚、一定要将孩子打掉,但鲁智妻子舍不得孩子,内心并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建议。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二舅心疼腹中已成人的侄孙,只好许诺说,等到孩子生下来,如果鲁智不改邪归正,全家人都支持他们离婚,并把孩子送给深圳的鸿霞表妹抚养,这才勉强说服了两位内心矛盾的老人,挽救了一个家庭。
2011年,面对鲁智无法摆脱的毒瘾,二舅和满舅痛下决心,主动报案,将他送去戒毒所,出来后,又通过女儿鸿霞的关系,将鲁智夫妇带去深圳上班。
很难想象,鲁智面临的数次婚姻危机,若不是二舅在其中的付出、周旋,一个家庭得以持续,腹中的孩子得以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鲁智最后因为亲情的召唤,痛下决心,改掉恶习,回归家庭,这其中,如果没有二舅持续的付出、爱心,也更是不可能的。对任何一个农村的大家庭来说,当他们面临种种困境时,若缺少家庭成员的担当和付出、妥协和让步、调解和劝说,很多矛盾就会累积和爆发,使本来脆弱的家庭不堪一击。
 1984年,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1984年,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二舅的担当,同样体现在村里一些公共事务上。
多年来,他一直担任村里的农技员,我童年印象中,二舅总是摆弄很多昆虫,尝试一些奇奇怪怪的捉虫方法,折腾一些专业含量极高的制种技术;同时他热爱读科普读物,关心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分田到户后,他曾参与组建、管理村里的教育基金会,这些工作不仅琐碎,也没有任何报酬。
1998年,村里的贫困户水球遇到了麻烦。他原本家境就不好,堂客(妻子)死了,崽疯了,属于村里的困难户,加上那年大风,房子也被吹倒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二舅原本计划自己建房子,但目睹了水球的情况,最后决定带领村人,筹钱筹人,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先帮水球建起房子。
后来我也发现,在隘口村,像舅舅这种热心的人还是不少,近几年来,村里为了抵御不好的风气对年轻人的侵蚀,提倡组建腰鼓队,玩龙、玩狮子、跳广场舞、很多村民一呼百应,“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该和别人说好话,就和别人说好话。隘口村是大家的隘口村,家家户户都有细伢子,风气好了,大人就可以少操一点心。”
令二舅欣慰的是,自2011年村里文化活动增多后,社会风气确实好转了很多,吸毒的少了,打牌的也少了;跳舞的多了,散步的也多了,村民有一种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归宿感,古老的村庄,开始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6
二舅晚年随女儿居住深圳多年,目睹女儿从一个乡村中学教师,跟随女婿到深圳立足,获得快速发展,更引发了他对时代的认同和感激。
女儿经济的优渥,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没有生下儿子的遗憾也早已被现实冲淡。
2016年4月,我去深圳探望两位老人,二舅兴致勃勃带我去看蛇口的招商大厦,告诉我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步伐,就是从此开始。在翠绿的南方街道,这栋已不光鲜、也不高大的建筑,显得落寞而渺小,但在二舅的眼中,却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
不得不承认,在时代的大潮中,这栋建筑和二舅的命运,确实产生了实际的关联――这是一个农民终究和时代产生了真实的交集。鸿霞表妹2004年定居深圳,抛弃单位,摆脱体制,依赖舅舅极富远见的教育投资和蛇口的开放条件,开始与外商做各类生意,最后和朋友合伙,开办电子厂,终究在深圳站稳了脚跟。
深圳房价的飙涨,让表妹的身价,早已超过所有家族成员的总和,以上种种奇迹般的变化,让二舅对深圳有了强烈认同。
我当然无法强求二舅知道更多的事情,无法告知二舅,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如深圳一样,但我同样无法否认,二舅基于个体经验,对时代判断的客观性。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时代转型过程中,部分受益农民的声音。
而更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二舅对现状极为满意,但他却没有沉浸在女儿营构的温馨、安逸之中。
多年来,他之所以一直坚持留在深圳,也是因为女儿、女婿的工作实在太忙,他和舅妈,不得不帮助独生女儿照顾孩子。孙子马上初中毕业,舅舅也临近七十,归家养老的迫切日甚一日。他内心真正念叨牵挂的,依然是隘口村的老宅和鲁家�那一帮亲人,对于村子近十年来遭受的外来冲击的巨大变化,他始终无法释怀。

面对隘口村败坏的风气,尤其是鲁智走过的弯路,令二舅常常心有余悸。尤其是村子里疯狂的“买码”,作为村庄的见证人,他目睹了这一怪胎侵入原本安宁土地的全过程,“最开始就是从靠近107国道的大荆、三江开始的。1998年,鲁家�就有人‘买码’,但没有形成规模,2001到2002年,‘买码’的人多了起来,2003年是疯狂发展期,霞姑娘就是这个时候栽进去的。到了2006年,是‘买码’失控期,所有人像疯子一样,看的是码,讲的是码,大人、小孩都‘买码’。‘买码’不知道害了很多人,买飞单、吃单让很多亲人撕破脸,还有好几个因为‘买码’想不通寻短路的”。
如果说“买码”直接从经济层面影响了村庄的后续发展,通过资金的外流抽空了隘口村的经济基础,那么,“吸毒”则不但从经济层面,更从精神和文化层面,给村庄带来了巨大的浩劫,这一毒瘤给村人带来的心灵灾难,根本无法从金钱层面计算。
直到今天,二舅依然感叹吸毒让鲁智走了很多弯路,“鲁智要是不吸毒,还是一个好伢子。他原本重情重义,又勤快,但自吸毒后,就彻底变了一个人,尤其是你满舅,不知道暗中吃了多少亏。吸毒真是害死人,鲁家�吸毒,三队死了两个,西山湾死了一个,六驼子家的孙子,在广州吸毒后被车撞死了。广州塘厦就是个吸毒点,鲁家�吸毒的伢子,都是从那儿学坏的,鲁智也是从那儿学坏的。”
至于赌博,则更是司空见惯了。近年来,赌博已主宰了隘口村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人际交往中最常见的方式,种种现象,都让二舅操心不已。尽管近两年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推行后,跳舞和打篮球已成为村人喜欢的娱乐方式。但二舅对鲁家�人天生的性格有更多警惕,“胆子太大,骑无疆马”,他担心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会一阵风式地烟消云散,担心“买码”、吸毒、赌博等恶习,一旦风吹草动,又会卷土重来。
7
不仅如此,耕作方式的迅速改变也令二舅惊讶不已。仅仅十几年工夫,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耕作方式就已被彻底抛弃,以往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再也难觅踪影。
一年两季变成了一季,插秧变成了抛秧,施肥再也不用家肥,以往的粪便是宝贝,现在却被视为农村巨大的污染源,除草也不用人工的方式,全部依赖除草剂,驱虫更严重,全部依赖效果明显的农药。更让二舅担心和迷惑不解的,是农村一直保留下来的各类农作物的种子,现在竟然面临绝迹的危险。“现在的田都不用家粪,化肥的使用太过分,土地已经弄得越来越贫瘠。最麻烦的是,现在的黄瓜、辣椒,栽了一年,第二年就不结种。我们以前都是自己留种,种了黄瓜,留一条大黄瓜,第二年就足够接着种;种了丝瓜,留一条大丝瓜,第二年丝瓜的种子就不用愁。今年留,明年种,世代如此,种子得以延续。但现在,那些土黄瓜、土丝瓜、土豆角、土茄子、土辣椒,都已经绝迹了。菜的味道,怎么样都比不上以前的味道。无论什么种子都要去公司买,以后万一没有种子了,该怎么办?”
当我告诉他,现在大部分种子,都被外国公司垄断,二舅更是忧心忡忡,“这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二舅的凝重,令我惊讶。
尽管二舅不止一次地明确表达,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好处,他对此心怀感激,但谈起村庄未来的命运,我发现他提供的方案,则是转头回到了集体时代。
二舅始终认为,村庄的良性发展,因寄希望于遇到好的领导人,寄希望于能够站在农民立场,为大众谋福利的干部和党员。
直到今天,他对80年代初期隘口村集体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良好势头,依旧念念不忘,“我们村,原本有可能建设成为湖南的华西村。当年隘口村出了一个好书记周树堂,带领村民第一个架电,第一个搞加工厂,给村里赚了很多钱,但后来对手污蔑他,将他击垮了,发展很好的加工厂也垮掉了。加工厂一垮,就没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就逼上缴、搬谷子、牵猪,上缴搞完了,领导就不找村里人了,也不管农民。后来的领导班子,竟然发展到分国家拨款五保户的钱、截留退耕还林的款项,更不要说水利款、直补金,甚至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对此,村民无权过问,都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新的干群关系,肥的是几个领导、受伤害的是几个农民,领导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步步恶化了。”
事实上,整个长乐的集体经济,在80年代初期,确实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尤其是保安设备的制造,全国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隘口村在当时的境况下,更是始终独占鳌头,“村民都富了,大家日子肯定更好过,但现在主要是干部不好,没有人愿意真正发展,只想自己捞一点就算了”,二舅再次强调。
在他心中,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显然比个别人过上好日子,更让人向往。他对时代的感激如此真实,他对未来的困惑也如此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