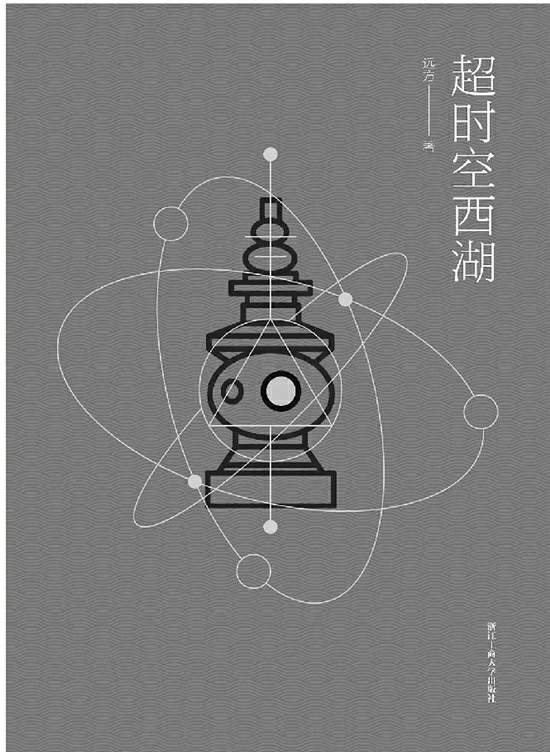原标题:林文月在虹口上学的两条路径,一条经过内山书店
一
说起林文月,文学爱好者也许知道,台湾大学教授,翻译过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她还是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的表姐。
最初读林文月的散文,是一篇写白令海阿拉斯加的冰山和浮冰的《白夜》,那时我正准备采访一个从白令海冰海捕鱼归来的远洋渔船船长。说实在的,船员出身的我熟悉中国沿海,但对酷寒的俄罗斯沿海所知甚少。读了林文月《白夜》后,对白令海有些了解――“近处,浮冰漂流,如猛兽、似奇禽,盛夏7月天,眼角因寒风而泪水流出,鼻尖和双耳也是冰凉的;远处,冰山巍巍峨峨,确荦嶙坚”。于是,采访时顺利多了。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虹口公共租界,日本侨民聚居的东江湾路。她们家离当时也住在虹口西江湾路的连战和其父母一家人不远。林文月与连战是表姐弟,她的外祖父,是连战的祖父,为《台湾通史》的作者、台湾爱国学者连横先生。
林文月先后就读于上海第一和第八日本“国民学校”,其中1937年因“上海事变”(“八一三”淞沪战争),迁往东京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上海,1946年2月赴台湾。前后12年在虹口居住。

青年时期的林文月
近来读林文月的一本散文集《生活可以如此美好》,有3篇写到在虹口上学。我试着根据这3篇文章提供的线索,对照《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和虹口地图,来还原她当年她上学的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从东江湾路到北四川路的第一国民学校,读小学一年级。林说,她家门口横亘着铁路轨道(应该是淞沪铁路),对面是虹口游泳池(在虹口公园西北角的东体育会支路上)。过铁轨后,绕过虹口游泳池和虹口公园后,向东拐入北四川路,然后朝南走一段路到学校。
第二条路径,从东江湾路到宝山路的第八国民学校,读小学二年级至五年级。从东江湾路拐入西江湾路,过公园坊再向下走,为六三公园。林说,走到六三公园,就是到学校路程的一半了。
林文月文章中的两条路径,均没有提到过桥,我想这两座学校应该在纵贯虹口中部的俞泾浦的东侧吧。
二
走第一条路径,林说,上学路上,在北四川路的方块石板铺的上街沿,不管一个人或者有同伴,她“总是顺着那石板跳行,有时也踢石子跳移”。在北四川路的尽头,有一排二层楼洋房,前段是果菜市场和杂货店等,后排是她喜欢去的地方,有一家文具店和一爿书店。但清晨上学时,书店还没有开门,她只能从玻璃窗望进去。小学一年级功课少,上午11:30就放学了。回家要等父亲回来午餐,不会太早开饭,所以她几乎每天在归途中溜进那爿书店“蹭”书看。爱看有插图的日文书。有时看书入神竟忘了肚子饿。书店的四壁全是书,门口有一收银台,轮流坐着一个日籍中年男子或老妇人,大概是母子。对她这个把书店当图书馆的小“顾客”,母子俩从无厌烦。她临走时,也会礼貌地向他们鞠躬道别。
某天下午,放学途中突降大雨,她从学校跑到书店避雨,全身湿透,被头顶不断旋转的吊扇一吹,打喷嚏了,身上发凉,似乎感冒了。但离家还有一段路,只能继续站着看书。此时,中年店主过来,示意她跟他上后面二楼房间。接着,老妇人上楼,提一壶热水,为她擦身,又拿出一套宽大的衣服让她替换。而后,他们铺了一个床,叫她躺下。

内山书店旧照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来了。老妇人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食叫她吃下去。中年男子问她家的住址和电话,老妇人叫她到隔壁房间换回她自己的衣服。原来她已将林文月的湿衣烘干了。中年男子打通电话后,过了一会儿,她母亲雇了一辆黄包车来接她。她母亲用日语向他们母子道谢,双方互相一再鞠躬。
1979年,林文月撰文回忆此事,心中充满温暖。她说她之所以后来一直与书结缘,与此童年经历大有关系。但她已记不起那爿书店的名字,那好心的店主人母子姓什么,也一直不晓得。
但就在前几年,她接受上海某报记者采访,说这爿书店叫内山书店,店主人母子当然是内山完造和他的母亲咯。众所周知,内山完造是鲁迅的至交,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反对中日战争的日本友好人士。他们母子对小朋友的关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三
走第二条路径,要经过六三公园,据《虹口文化志》,其位置在西江湾路240号,为日式庭院,今已不复存在。园内有绿茵草地,花木假山,潺潺流水,春天樱花甚灿,还养了一些小动物。如果早上上学时间早些,林文月会和她的同伴一起进园逛一圈。
上学的路上,她还常常看到日本兵野蛮地用刺刀乱翻乱戳卖水果人的摊子,弄得水果满地滚,小贩只得跪地求饶。这样肆无忌惮的恶行,日本女同学竟污蔑说:“支那人很坏,我爸爸说,他们时常藏手榴弹在水果堆里。”
清廷通过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于1895年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就把它当作殖民地来治理,强迫台湾儿童学日语,实行奴化教育。故林文月对自己的身份也搞不大清楚。

在写东西的林文月
但到抗战末期,第八国民学校驻扎进日军。有一次,在防空壕里,一个日本兵与她们交谈,问起了大家的籍贯,回答的有东京、大阪、熊本等。问到林文月时,她迟疑地说:“我是台湾人。”那个日本兵一愣,马上变得异常冷漠,不再理睬她,这次她幼小的心灵明白了,在日本兵的眼里,台湾人也是异类。
她开始明白台湾人在上海的尴尬地位。然而,从小在虹口接受日语教育,却为她日后熟稔地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虹口的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低声下气,畏畏缩缩,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飞扬跋扈。台湾人陷入两难境地,我们是战败方呢,还是战胜方呢?接着,虹口的台湾人都分发到一面中国国旗。台湾人互相告知,赶紧把太阳旗烧了,插上“青天白日满地红”。
但因为林文月父亲在日本公司任职,时不时有人寻上门来,说他们是汉奸。
1946年2月,林文月举家乘船在黄浦江的寒雾中启航回台湾。
林文月曾说过她有三种文笔。她不仅是散文家、翻译家,亦是一位学者。她所著的研究六朝文学和文人的《谢灵运》《山水与古典》,近年大陆的三联书店已出版。现在我的书架里就有这两本书。